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新加坡國立大學 古正美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頁159-201
©2000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臺北市
| 頁159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五期(2000.07) |
提要
筆者於本文中申釋了南印度烏荼國王進獻給唐德宗的烏荼版《華嚴經》,係在觀音佛王傳統的影響下於烏荼國所集結而成的。觀音佛王傳統,亦即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是由南印度的金剛乘學派於六世紀末葉所建立的。為了解釋烏荼版《華嚴經》的集結背景,筆者同時也描述了七世紀後《華嚴經》及觀音佛王傳統在中國及南海的發展與傳播。
關鍵詞:華嚴經、不空羂索觀音、佛王、金剛乘、意識型態
| 頁161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序言
雖然許多學者在其著作中都提到第八世紀末南天烏荼王 (King of Orissa)進獻唐德宗(780-805)《華嚴經》的事,然到目前為止,還沒見有專作討論南天烏荼版《華嚴經》發展的背景及意義。過去的學者在談論烏荼版的《華嚴經》之際,基本上都從此版宗教及文字的發展情形去談論此版出現的意義,而沒有從佛教意識形態的發展角度來探討其出現的歷史、文化背景及流行的狀況。譬如,呂澂在其《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便如此提到烏荼版《華嚴經》發展的意義;「還有,普賢行願的樞紐在於始終一貫的『願心』,這一點在華嚴思想發展到四十卷《華嚴》的階段最為突出,賢首創宗的時候還未及知道,便也不免忽略了。」[1]此處所言的四十卷《華嚴》,即指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或文中所言的烏荼版《華嚴經》。由于學者對烏荼版《華嚴經》討論不多,因此,筆者認為我們在研究佛教意識形態在亞洲發展及傳播的情形之際,有從新的角度重新研究此烏荼版《華嚴經》的必要;特別是此版的《華嚴經》有反映南天在七世紀之後所使用的《華嚴經》佛王傳統(the Avataṃsaka
* 送審日期: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八日。
1.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台灣里仁書局,1995,頁391。
| 頁162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Buddharāja tradition)及密教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the Amoghapāśa Buddharāja tradition)的內容。
烏荼版《華嚴經》在烏荼的出現,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現象。造成此歷史現象的原因,乃是第六世紀末期之後在南天出現及發展的金剛頂派(the Vajrasekharayāna )造成的結果。過去的學者都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也沒有注意到,烏荼版《華嚴經》的出現,也說明了七、八世紀之後,《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在南天、南海諸國及中國都有同時發展及流通的現象。
譬如,喬治。謝得士(George Coedes )在談論東南亞的天王傳統(the Devarāja tradition) 及 佛王傳統(the Buddharāja tradition)之際,只認為,東南亞的天王傳統乃是受印度教影響的「帝王信仰」(royal cult)。[2]他不但不知道,東南亞所施行的天王傳統及佛王傳統,是印度教(Hinduism) 及佛教(Buddhism)的教化傳統(inculcation tradition),或帝王使用以治國的意識形態(political ideology),而且也不知道,此二教化傳統在七、八世紀之後,乃是南天金剛頂派傳入南海諸國及亞洲其他地方的兩種不同宗教系統的教化傳統。謝得士更不知道,第七世紀之後由南天傳入亞洲各地的佛王傳統,還有《華嚴經》佛王傳統及密教觀音佛王傳統之別;甚至不知道,由南天傳入的密教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還是金剛頂派自己在南天一手造成及發展的觀音佛王傳統。[3]
除了謝得士之外,目前研究東南亞佛教藝術史的學者,在談論第七世紀之後的彌勒菩薩(Bodhisattva Maitreya)或彌勒佛(Buddha Maitreya) 造像及觀音菩薩 (Bodhisattva Avalokiteśvara)造像之際,也都不知道,許多此類的造像,都是此些地區的帝王之佛王造像。譬如,南達那•楚提旺 (Nandana Chutiwongs)與丹尼士•帕翠•萊地 (Danise Patry Leidy) 在其等所著的《未來佛》 (Buddha of the Future) 一書中,在談論東南亞的彌勒菩薩信仰及造像的情形時,都沒有提到其等所談的彌勒菩薩像,乃是東南亞帝王在施行《華嚴經》佛王傳統下所造的彌勒佛王造像。[4]又如,約翰。密細 (John Miksic) 在其《婆羅婆多》一書中談論第八世紀建造的爪哇(Java)婆羅婆多(Borobudur)
2. George Coedes, Walter F. Vella (ed.).Susan Brown Cowing (tra.),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p. 100-101.
3. 同上,見全書。
4. Nandana Chutiwongs and Denise Patry Leidy, Buddha of the Future-An Early Maitreya From Thailand, Singapore: Sun Tree Publishing, 1994. 見全書。
| 頁163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佛教遺址上的《華嚴經。入法界品》的造像時,也沒有解釋為何此遺址要花費百幅以上的石雕造像建造《入法界品》之彌勒菩薩信仰的造像。[5]
另一方面,研究金剛頂密教信仰的學者,如木村西崖,在研究金剛頂在南天的發展情形之際,雖然注意到金剛頂與南天發展出來的瑜伽蓮花部行法有直接的關系,然他也不知道,南天瑜伽蓮花部的成立,就是金剛頂成立及發展的主要原因。他更不知道,南天金剛頂蓮花部的主要信仰,即是不空羂索觀音(Avalokitesvara Amoghapasa)的信仰,而此信仰乃是受南天印度教天王傳統之影響而產生的密教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因此,他在談論金剛頂的「佛頂金輪」此詞或「佛頂輪王」此詞時,都不知道為何金剛頂有這種佛與轉輪王同體或同身的信仰現象。所謂「佛與轉輪王同體」的信仰,就是「佛即是轉輪王」(He who is Buddha is cakravartin),或「轉輪王即是佛」的「佛王」(Buddharaja)信仰。[6]
過去的種種佛教研究情形都說明了,有許多佛教的發展現象,我們是必須從佛教意識形態的發展及使用角度去瞭解其真實的狀況,否則我們是無法明白這些現象出現的原因。因此在此文中,筆者便要自烏荼版的《華嚴經》談起,企圖說明此烏荼版《華嚴經》出現的真正原因,及金剛頂的信仰發展及傳播於東南亞的情形。由于本文所牽涉的問題相當多,且複雜,因此,文中對某些問題的說明,只能就與本文有關者作發揮,而不作全面的解說。譬如,對金剛頂信仰的說明就是一個例子。
筆者在作〈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7]一文時,因鑒於武氏施行《華嚴經》佛王傳統的經文及僧人都傳自于闐 (Khotan),及古代的于闐王有崇信《華嚴經》,甚至使用《華嚴經》佛王傳統的現象,因此在《武則天》一文中,筆者并沒有談論南天烏荼版《華嚴經》的發展性質。故此文可以作為研究七世紀之後亞洲各地發展《華嚴經》佛王傳統的補充。筆者在《武則天》一文中因對《華嚴經》佛王傳統的發展理論及武則天使用的情形已有詳細的說明,故於此文,對此佛王傳統不再贅述。本文在此所言的南天,乃指南印度,而南海諸國,則指今日的東南亞諸國。
5. John Miksic, Borobudur--Golden Tales of the Buddhas, Bamboo Publishing Ltd.., 1990.見全書。
6. 木村西崖,《密教發達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3 (台灣版)。見上冊如,頁294-295等或全書。
7. 見拙作,〈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國學研究》,第七期。
| 頁164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烏荼《華嚴經》的進獻者及烏荼佛教
南印度烏荼王進獻《華嚴經》給唐德宗的前後經過,中國的佛教文獻有多處記載。譬如,釋般若主持翻譯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即烏荼版《華嚴經》,之〈出經後記〉便如此記:
南天竺烏茶國,深信最勝善逝法者,修行最勝大乘行,吉祥自在作清淨師子王,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大自在師子中大王,手自書寫大方廣佛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親近承事佛剎極微塵數,善知識行中五十五聖者,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謹奉進上。伏願大國聖王福聚高大超須彌山,智慧深廣過四大海,十方國土通為一家……[8]
此〈出經後記〉說得很清楚,當時南天竺烏荼國王「吉祥自在作清淨師子王」因信奉大乘,而手自書寫《大方廣佛華嚴經》進獻大唐天子「大吉祥天子大自在師子中大王」。當時的烏荼國,一般都認為是現在東南印度的「奧里薩」(Orissa)。[9]雖然當時烏荼王的名字被記為「吉祥自在作清淨師子王」,然此名和文獻所記之大唐天子的名字「大吉祥天子大自在師子中大王」,一樣非其朝代名稱。到底此位烏荼王又是誰?現代學者曾對此烏荼王作了一些研究,其結論大致如下:
德巴拉。密特拉(Debala Mitra) 在其書《烏荼之阿處特拉吉普的銅器》提到烈微 (S. Levi)之說,並認為,進獻《華嚴經》的烏荼王(King of Oḍra or Orissa)是包馬•卡拉王朝(Bhauma-Kara dynasty) 的奠基者素巴卡拉德瓦第一(Śubhakaradeva, 1)。[10]而馬君達(R. C. Majumdar)則認為,是素巴卡拉德瓦第一的父親濕婆卡拉第一(Sivakara, I)與素巴卡拉德瓦第一一起進獻。[11]素巴卡拉德瓦第一至少有兩位繼承者,即濕婆卡拉德瓦 II (Sugatasraya Śivakaradeva II) 及素巴卡拉德瓦 II (Parama-saugata Śubhakaradeva II),他們都是眾所周知
8. 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出經後記〉,《大正》卷10,頁848下。
9.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14。
10. Debala Mitra, Bronzes from Achutrajpur, Orissa,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1978, p. 12.
11. Ibid., see also, R.C. Majumdar, The Age of Imperial Kanauj, Bombay, 1955, pp. 64-65.
| 頁165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的佛教信徒。這些包馬•卡拉王朝的佛教帝王,不僅對大乘佛教都相當熟悉,而且也花費相當的財力促使佛教發展。包馬•卡拉王朝的都城乃在加普(Jajpur),而加普附近就有許多包馬•卡拉王朝的帝王所遺留下來的佛教遺址。包馬•卡拉王朝奠基的年代,至今學者尚爭論不休。最初學者都將其定於公元606年,但西爾卡(D. C. Sircar) 現在則將之定於公元831,而馬君達則將其定在第八世紀的中期。拉加古魯(Satyanarayan Rajāguru)用天文學的證據將其定在736,這與烏荼王於795進獻《華嚴經》的時間相近。包馬•卡拉王朝統治烏荼的時間共兩百多年,[12]此時代佛教造像包括佛像、度母或多羅像(Tārā)、世界主(Lokeśvara)、彌勒像(Maitreya)、文殊師利像(Mañjuśrī)、寶藏神像(Jambhala)及金剛薩埵像(Vajrasattva)等密教造像。[13]在都城加普,甚至出土一尊高達4米77.5公分,烏荼最高的蓮花尊(Padmāpaṇi)或觀音造像。[14]
周一良在研究開元四年(716)來華的僧人善無畏(Śubhakara)時,[15]因善無畏「其先自中印度,因國難分烏荼 (Odra),父曰佛手(Buddhakara)王」之事,也提到包馬•卡拉王朝,並認為善無畏與獻《華嚴經》的烏荼王有關。他說:
……據玄奘(Watters, 1.238)及道宣 (T50,432a 20),據說烏仗那 (Udyāna)國王曾是一位背井離鄉的「釋迦」(śākya)。由于 Udyāna 譯法甚多,其中就有烏荼或鄔荼 (崛,205-206),因此,善無畏家族的故事可能是對應于 Oḍra 的烏荼與對應于 Udyāna 的烏荼之間的某種混淆。《碑》已有這種情況。公元八世紀的後二十五年間,在 Oḍra 存在過一個王朝,國王的名字中都有「kara」,有一位甚至就叫 Śubhakara, 他們都信奉佛教。依據在奧里薩發現代銅卷銘文和漢文材料可以推求出這些「kara」王的年代。(參見 S. Lévi《奧里薩的 Śubhakara 國王》,(King Śubhakara of Orissa, Epigraphia Indica), 15.8.363-4; R. D. Banarji, History of Orissa, 1.146-160)。由于善無畏被稱為 Śubhakara,因此其父的名字可以復原為 Buddhakara, 我傾向于推測他們是這些「kara」王的祖先。[16]
12. Ibid., Bronzes from Achutrajpur, Orissa, p. 16.
13. Ibid., p. 14.
14. Ibid.
15. 宋贊寧等奉敕撰,《宋高僧傳•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大正》卷50,頁715中。
16.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教》,頁14-15,及頁129-130。
| 頁166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善無畏如果如周一良所言來自包馬•卡拉王朝,此王朝的崛起,就應該是在開元四年之前,即第八世紀初期之前,而進獻《華嚴經》的烏荼王就不可能如烈微及德巴拉。密特拉所說的,是包馬•卡拉王朝的奠基者或其父親。因為善無畏來華的年代與印度學者所說的進獻《華嚴經》的年代或包馬•卡拉王朝的開創年代相去近百年。包馬•卡拉王朝,就文獻的記載,乃是一處發展大乘佛教的地方。烏荼大乘佛教的發展,事實上早過善無畏來華的時代。玄奘(600-664) 于第七世紀中期去烏荼時所見到的景象已是:「烏荼國周七千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并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四,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并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17]既是如此,烏荼大乘佛教的發展在第七世紀前半期已是非常盛行。包馬•卡拉王朝的興起,由于文獻不足,我們不知道其是否能倒溯至第七世紀的中期,甚至更早?如果不能,玄奘所見的烏荼佛教,應是另一烏荼王朝所推動的大乘佛教。
七、八世紀南天密教金剛頂的發展概況
就目前學者所瞭解的烏荼,在第八世紀初期已是一處南天密教金剛頂派的發展中心。大村西崖在其《密教發達志》中談到密教金剛頂派在南天發展的情形時說:
金剛頂法者,蓋成于南天烏荼、摩賴耶、師子等國。想寶覺阿闍梨成其先聲,與大日經成于中天摩竭陀國那爛陀寺不同。其事教兩相所以大異於胎藏法,實在乎茲。[18]
大村西崖之所以知道八世紀南天烏荼、摩賴耶(Malaya)及師子(Sri Lanka錫蘭)等地成為當時印度密教金剛頂派的發展中心的原因是,開元八年(720)來華發展密教金剛頂派的大師金剛智(Vajrabodhi,661-732),就是摩賴耶人。[19]與金剛智同時到達洛陽的另一位密教金剛頂派大師不空金剛
17. 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頁812。
18. 大村西崖撰,《密教發達志》,上冊,頁492-493。
19. 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釋跋日羅菩提傳》,卷一,《大正》卷50,頁711。金剛 智死於開元二十年(732),壽七十一。
| 頁167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Amoghāvajra, 705-774),在有些文獻中也被記為師子國人。[20]不空來華之後,於開元二十九年(741)奉其師金剛智之命,回到師子國向普賢阿闍梨學習密教金剛頂瑜伽法門。《宋高僧傳。不空傳》說:「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並許含光、慧■[功/言]等同受五部灌頂。空自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式、色像、壇法、幖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21]
當時的師子國或錫蘭,一定和南天的烏荼及摩賴耶一樣,都是密教金剛頂派的發展中心,否則不空不會奉金剛智之命,在後者去世之後還有師子國求法之行。[22]木村西崖對師子國發展密教金剛頂瑜伽的評價甚高,他不但認為,「寶覺阿闍梨」,即不空到師子國求法的「普賢阿闍梨」,是密教大師金剛智的灌頂師,而且也是南天密教金剛頂的開山祖。他說:
所謂本師寶覺,乃定為金剛智受灌之阿闍梨,其事明瞭的確,莫可復疑而已。是時寶覺在師子國,師子國與摩賴耶,一衣帶水耳,其或游行以在王寺,亦不容疑。智之受法於南天竺,乃如所傳。其所受五部灌頂者,既金剛頂法,而其曼荼羅為金剛界,固莫論也。然而趙遷、嚴郢、呂向等為俑,後人皆承其謬,遂無復檢千缽經序,以考覈之者。又未曾聞有唱寶覺即龍智之說者。迨今傳金剛頂法者,竟不曉根本先師有寶覺阿闍梨者,是豈得不慨乎?[23]
一般的中國文獻及學者,都以金剛智為中國密教的創始者。譬如,贊寧在其所撰的《高僧傳》卷三後便如此記密教金剛頂的教法及承傳情形:
……二密教者,瑜伽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也……次二教令輪者,即密教也。以金剛智為始祖焉……傳教令輪者,以秘密傳秘密……[24]
20. 西京西明寺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不空三藏行狀》,卷十五,《大正》卷55,頁881上。
21. 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頁712,亦見唐趙遷撰,《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傳》,《大正》卷50,頁293上。
22. 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釋跋日羅菩提傳》,卷一,頁712上。
23. 木村西崖撰,《密教發展志》,上冊,頁472-74。
24. 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卷三,頁724中。
| 頁168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趙遷在其所撰的《不空傳》中甚至如此提到金剛頂派法師承傳的系譜:
昔者婆伽梵毗盧遮那以金剛頂瑜伽秘密教王真言法印付屬金剛手菩薩,垂近千載,傳龍猛菩薩,數百年後,龍猛傳龍智阿遮梨。後數百年,龍智傳金剛智阿遮梨耶。金剛智今之大師,雖源一流,派分蓋數十人而已,家嫡相繼,我師承其六焉。[25]
大村西崖認為,中國學者說金剛智傳龍智之金剛頂法的說法是錯誤的。據他的說法,金剛智的金剛頂法乃是傳自師子國的「寶覺阿闍梨」。無論其真實情形如何,第八世紀中期左右,師子國也是大師輩出的金剛頂密教發展中心。
烏荼成為密教金剛頂的發展中心之一,也有文獻記載。主持翻譯烏荼版《華嚴經》的釋般若,在建中二年(781)來華之前,「既而聞南天尚持明藏,遂便往詣諮稟乎所未聞。烏荼王寺有灌頂師達摩耶舍,般若就而受瑜伽教入曼陀羅,傳三密謢身,五部契印。」[26]此處所言的「烏茶」(Orissa),指的就是此文所說的「烏荼」。由此可知,第八世紀的烏荼、摩賴耶及師子等地,已是南天密教金剛頂派的發展中心。
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the Amoghāpaśa Buddharāja tradition)的信仰基礎
密教金剛頂派在南天發展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的史實,可以從唐高宗永淳二年(683)遣使到南天請來發展密教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的專家菩提流志(Bodhiruci)一事證明之外,[27]金剛頂派制作的瑜伽經典亦能證明。
菩提流志是在武氏長壽二年(693)抵達神都洛陽。菩提流志一到洛陽,武氏便馬上請他主持《寶雨經》的譯經工作。[28]菩提流志所譯的《寶雨經》,
25. 前試左領軍衛兵曹參軍輸林待詔臣趙遷撰,《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頁292中。
26. 圓照撰,《貞元錄•釋般若傳》,卷十七,頁894下;亦見木村西崖,《密教發達志》,下冊,頁736。
27. 高宗及武氏遣使請來南天菩提流志的事,請見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菩提流志傳》,卷三,頁720中。菩提流志在武氏時代發展密教不空羂索觀音傳統的細節,筆者將另文介紹。
28. 宋贊寧等奉敕撰,《宋高僧傳•釋菩提流志》,頁720中。下;并見唐天竺三藏達摩流支(菩提流志)譯,《佛說寶雨經》,卷二,《大正》卷16,也292中。
| 頁169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有兩段經文是當時菩提流志等翻譯者加入經中,作為說明武氏當時要以「阿鞞跋致」或「不退」(avivaitika)之八地菩薩及轉輪王(cakravartin)形象統治大周(690-705)的流通物。武氏在《寶雨經》中加入的這兩段經文,也是武氏要通告天下,其將放棄正在使用的《華嚴經》佛王傳統及彌勒佛王形象,而代之使用「不退」菩薩的佛王面貌治世。從《寶雨經》并不能看出武氏當時使用的八地菩薩面貌為何。但自同年武氏敕菩提流志、慧智及寶思惟三人翻譯三部不空羂索觀音經典的情形來判斷,當時武氏所使用的佛王傳統及佛王形象,乃是密教不空羂索觀音的佛王傳統及佛王形象。這說明,菩提流志從南天帶來中國的佛王傳統,確實是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29]
武氏一面要以不空羂索觀音的面貌面世,一面又要以轉輪王的面貌面世。這種又是觀音又是轉輪王的「神、我一體」的信仰,就是南天不空羂索佛王傳統的基本信仰。南天金剛頂在發展這種「神、我一體」的信仰理論時,並不是沒有在其所造的經中作解釋。
第八世紀不空翻譯的《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蓮花部念誦法門》,便提到瑜伽觀法有蓮花部或觀音觀法。此《經》在說明瑜伽行者應如何修行蓮花部或觀音觀法時說:
……以是印咒灑身衣,咒水澡浴及著衣等并得通用。若浴之時,當一心憶佛菩薩等,勿令散亂,想于本尊與自身無異而浴。初想本尊及三寶等如在目前,用所浴水三掬而獻,是印當以二手如常為掬。[30]
南天瑜伽蓮花部的這種觀法,也見記於不空所譯的另一部蓮花部經典《瑜伽蓮花部念誦法》。該《念誦法》說:
隨誦真言,以右大拇指向身招之,即成召請,即觀本尊心上有圓滿寂靜月輪,於月輪中右旋安布陀羅尼字,其字皆放白色光遍周法界。其光還入行者頂,于瑜伽者心月輪中,……準前作觀,如是觀已,修瑜伽者自身與本尊觀自在身,等無差別,如彼鏡像不一不異。[31]
29. 見拙作,〈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及佛王形象〉;詳細情形并見另文說明。
30. 不空奉詔譯,《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蓮花部念誦法門》,《大正》卷20,頁2。
31. 不空奉詔譯,《瑜伽蓮花部念誦法》,《大正》卷20,頁6上。
| 頁170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不空所譯的此二部南天瑜伽蓮花部經典,都提到觀音與行者二而為一的「神、我合一」的修行法。《觀自在大悲成就瑜伽蓮花部念誦法門》很清楚的說,瑜伽行者甚至在洗澡時,「當一心憶佛菩薩等,勿令散亂,想于本尊與自身無異而浴」,而《瑜伽蓮花部念誦法》也說,「修瑜伽者自身與本尊觀自在身,等無差別,如彼鏡像不一不異」。這種「神、我同體」的瑜伽觀法用在使用佛教統治世間的轉輪王(cakravartin)或法王(dharmarāja)身上,就成為金剛頂成立的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的信仰基礎。在此信仰之下,觀音便是轉輪王,轉輪王便是觀音。
木村西崖在談到金剛頂的瑜伽觀法時,特別提到此觀法為南天密教發展的特色。他說:「瑜伽觀法者,如心地觀經及羂索經所說觀想即是,蓋南天密教特色。」[32]由于此瑜伽觀法與其轉輪王或佛王的信仰有關,因此此瑜伽亦有「輪王瑜伽」之名。不空翻譯的《金剛頂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就是一部談論「輪王瑜伽」的經典。在此《經》中,經文甚至提到輪王的三種坐相。[33]此《經》所提到的輪王三種坐相,「交腳、垂一及獨膝豎」,[34]都是歷史上佛教轉輪王常用來造自己的轉輪王坐相的造像模式。[35]
金剛頂的瑜伽觀法,除了由「輪王瑜伽」這樣的概念可以看出此觀法與其發展的觀音佛王信仰,即「佛即是王」,「王即是佛」,有關之外,其佛王信仰的內容,在 「金輪佛頂」類的經典或概念也表露無遺。所謂「金輪佛頂」,木村西崖說:「惟金輪佛頂者,佛與國王之合成,出於會融王、佛二法之思想。」[36]換言之,「金輪佛頂」就是金剛頂「佛王」信仰的基本概念。在金剛頂的信仰中,「金輪佛頂」也稱為「佛頂輪王」。菩提流志所譯的《一字佛頂輪王經》即提到,如來如何變化成轉輪王身或佛王身的事:
如來今日何故特化大轉輪王(輪王)身,大光明聚?甚奇希有,本未曾見。如來誥言:大善男子,此是一字佛頂大法輪王,執持諸佛形相,神變三摩地門。大善男子,譬如汝等集大壇現種種威德諸神變像不思議
32. 木村西崖,《密教發達志》,上冊,頁328。
33. 不空譯,《金剛頂一字頂輪王瑜伽一切時處念誦成佛儀軌》,《大正》卷19,頁320-327。
34. 同上,頁326。
35. 參見拙作,《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台北:允晨文化,1993,第八章。
36. 大村西崖,《密教發達志》,上冊,頁295。
| 頁171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事。如來亦爾,如是振現大法輪王特奇色身姿貌威德。[37]
很顯然的,「佛頂輪王」的概念,就是「佛王」的概念。此概念的出現,就是行瑜伽觀法的結果。因此,金剛頂的佛王信仰,在其所造的經典是有跡可尋。「佛頂輪王」也有「明咒」,而此「明咒」的功用,就是如「佛王」以佛教治理世間,使世間安樂,得無量福的功用。菩提流志所譯的《五佛頂三昧陀羅尼經》即如此提到「佛頂輪王明咒」的功用:
……汝今諦聽一字頂輪王明咒王法……此等咒王是如來手足,是如來唇是如來口。轉輪法王作大利益一切有情,若此世界一切菩提等及諸天人等,能依法讀誦授持是一字輪王頂明者,所有一切諸天世人種種鬼神,悉無能害作諸破壞,以是當得一切安樂,受無量福,行大慈悲,住不退地,無諸惱疾火水刀王等難……[38]
金剛頂提出「佛頂輪王」的信仰,當然與其成立的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有絕對的關系。但,包括木村西崖在內的學者,於討論此「佛頂輪王」信仰時,都不知道為何金剛頂要提出這樣的信仰,因此都沒有進一步的解說。[39]由于過去都不知道金剛頂的文化以佛王文化之發展為主,因此,我們對七、八世紀之後亞洲各地許多佛教發展現象,都只是看到現象,不知其出現的原因。
金剛頂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的「金輪佛頂」發展特色,便不見於同一時代流行的十一面觀音信仰典籍。譬如, 北周明帝(557-560) 時代初譯的《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便未記有此種神、我同體的觀音信仰。此《經》在說明行者與觀音的關系時只說:「願現身即得隨逐觀世音」,[40]而沒有說行者與觀音同體。由此可知,南天所發展的觀音信仰及行法,與第六世紀所發展的十一面觀音信仰及行法有顯著的區別。
金剛頂成立的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除了散見於其所造的經典之外,也見證於南天及南海帝王使用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治國的實例。金剛頂為何會成立這種「神、我同體」的密教觀音信仰?這與南天當時盛行的印度教
37. 大唐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一字佛頂輪王經》,卷一,《大正》卷19, 頁227。
38. 同上,《五佛頂三昧陀羅尼經》,卷一,《大正》卷19,頁264中。
39. 木村西崖,《密教發達志》,上冊,頁295。
40. 北周耶舍崛多譯,《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卷三,《大正》20,頁151。
| 頁172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天王傳統有極大的關系。
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與南天的天王信仰
天王傳統原是印度教的一種教化傳統。此教化傳統和佛教的佛王傳統皆衍自於古代印度大王阿育王(King Asoka)所創立的轉輪王治世傳統,只是天王傳統與佛王傳統都是後來發展的密教化(esotericised)之帝王教化傳統。中國《宋書。夷蠻傳》、《梁書。諸夷傳》及《南齊書。蠻傳》中即載有南海扶南國(Funan, 古代柬埔寨)及南亞各國行天王制,信仰摩醯首羅的情形。中國的史料及佛教文獻稱摩醯首羅(Maheśvara)為「天神」(deva) 、「天王」(devarāja).或「大自在」(lokeśvara)。早期許多經典都視摩醯首羅為印度教神祗濕婆(Siva)。天王傳統在發展的過程中,有視天神與王(raja)不同體者,也有視天神與王同體的信仰。天王傳統有印度教及佛教兩種。中國石虎時代所施行的天王傳統,就是佛教的天王傳統。[41]
第七世紀南天許多地區一直都是印度教天王傳統或摩醯首羅天信仰發展的地方。譬如,我們在此所言的「烏荼國」,雖然《大唐西域記》記其:「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但也有「天祠五十所, 異道雜居」的現象。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發源地「秣羅矩吒國」(摩賴耶),[42]更是「天祠數百」,外道甚眾,多露形之徒」的地方。[43]《大唐西域記》在此所言的「天祠」,指的就是印度教天神摩醯首羅或濕婆(Siva)的神廟。
濕婆在印度教神壇上常被視為印度教三大主要神祗之一。濕婆具有正面的個性,也具有負面摧伏的個性。摩醯首羅進入早期的雜密經典時,也將這種濕婆的摧伏個性帶入佛經。譬如,東晉所譯的《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便如此記摩醯首羅的摧伏力量:「我過去從諸佛所得聞說此大神咒名,從是以來,神通自在,遍領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鬼王皆屬我,我有神力悉能摧伏。」[44]黑爾(J. C. Harle) 也提到,印度南方特別喜歡令人畏懼的濕
41. 以上有關天王傳統的說明,請參見拙作,《東南亞的「天王傳統」與後趙時代的「天王傳統」》,《佛學研究》,第七期 (1998),頁300-322。
42. 見後詳述。
43. 季羨林等校注,玄奘、辯機原著,《大唐西域記校注》,頁857,〈秣羅矩吒國〉。
44. 東晉帛尸梨蜜多羅譯,《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卷三,《大正》卷21,頁550上。
| 頁173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婆形象。[45]
金剛頂的發展場所,事實上也是摩醯首羅或天王信仰發展的地方,因此,金剛頂的信仰受印度教天王信仰的影響乃意中之事。
不空羂索觀音的「聖山」補陀洛迦山
南天發展不空羂索密教觀音信仰的事見諸佛教文獻。中唐之前所譯的不空羂索觀音經典,都說不空羂索觀音住在補陀洛山(Potala)。換言之,不空羂索觀音的發展中心即在補陀洛山。中國最早翻譯的不空羂索觀音經典乃是隋代(581-617)闍那崛多所譯的《不空羂索咒經》。此《經》說:「一時,婆伽婆(bhagavat)在逋多羅山頂觀音宮殿所居之處。」[46]唐代玄奘所譯的同經異譯《不空羂索神咒心經》則將觀音的「聖山」之名譯為「布怛洛迦。」[47]菩提流志翻譯的《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則一再的說;「若苾芻、苾芻尼、國王、大臣一切人民悻欲求見觀世音菩薩補陀洛山寶宮殿中」。[48]不空翻譯的《不空羂索陀羅尼儀軌經》也說不空羂索觀音所自居之處在「補陀洛山」。該《經》說,「爾時觀世音菩薩摩訶薩,說此真言之時,其補陀洛山……皆六種震動。」[49]
不空羂索觀音所居之處,不是佛經造出來的名字,其乃是南天摩賴耶國(Malaya)附近的觀音「聖山」。《大唐西域記》說,「布呾落迦」(Potalaka 補陀洛迦)是在秣羅矩吒國(Malakuta)秣剌耶山東,由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僧伽羅國路」。[50]《續高僧傳。釋玄奘傳》也說:「秣羅矩吒國即瞻部洲最南濱海境也」。[51]印度學者艾耶(Subrahmanya K. V. Aiyer) 認為,秣羅矩吒 國,即淡米爾文碑銘中的馬來那度(Malaināḍu)。[52]僧伽羅國(Siṃghala or Siṃhala),
45. J. C. Harle,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67.
46.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不空羂索咒經》,《大正》卷20,頁399上。
47. 唐玄奘譯,《不空羂索神咒心經》,《大正》卷20,頁402中。
48. 唐菩提流志譯,《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二十二,《大正》卷20,頁346上等處。
49. 師子國三藏阿目佉奉詔譯,《佛說不空羂索陀羅尼儀軌經》,卷下,《大正》卷20,頁437中。
50. 見季羨林校注,玄奘、辯機原著,《大唐西域記校注》,頁857-863,「秣羅矩吒國」。
51. 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釋玄奘傳》,卷四,《大正》卷50,頁452中。
52. Subrahmanya K. V. Aiyer, Historical Sketches of Ancient Deccan, Madras, 1917, Vol. One, pp. 119-121. 也見 季羨林等校注,《大同西域記校注》,頁858。
| 頁174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就是師子國或執師子國,即今日所言的錫蘭或斯里蘭卡。[53]由《大唐西域記》所記的「布呾落迦」地望來看,不空羂索的「聖山」, 乃在離獅子國不遠的南印度地方或摩賴耶國附近。《宋高僧傳。釋跋日羅菩提 ( 金剛智)傳》在說明金剛智是南印度摩賴耶國人時也提到:「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華言光明。其國境近觀音宮殿補陀洛迦山。父婆羅門,善五明論,為建支王師。」[54]《開元錄。跋日羅菩提傳》在注明金剛智乃印度摩賴邪國人時也說:「此云光明國,其國近觀音宮殿補陀落山。」[55]由此可知,觀音菩薩的「聖山」「布呾落迦」,的確是在古代的「秣剌耶」或「摩賴耶」附近。《大唐西域記》如此記「布呾落迦山」的情形:
秣剌耶山東有布呾落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歧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帀,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為涂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56]
上面的文獻說得很清楚,第七世紀南天金剛頂的發展地「摩賴耶」,就是密教不空羂索觀音信仰的發源地。《大唐西域記》所記的第七世紀「摩賴耶」發展大乘佛教的情形,因此即是金剛頂發展密教的情形,而此金剛頂發展密教的特色,就是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的特色。金剛頂既在南天摩賴耶發展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金剛頂的其他兩個發展中心,烏荼及師子國,也應是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的發展地。
在過去,學者一般都沒有將金剛頂的信仰與不空羂索觀音的信仰視作同一體系的信仰。因此,每當談到金剛頂的信仰時,便將之與不空羂索觀音的信仰用「純密」與「雜密」二詞區分。這種作法乃有商榷的餘地。事實上大村西崖在談到(不空)羂索經所從屬的派別時就已說:「羂索經乃屬南天的瑜
53. 見季羨林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頁857-863,「秣羅矩吒國」,頁866-67。
54. 《宋高僧傳•釋跋日羅菩提傳》,卷一,頁711中。
55. 《開元錄•沙門跋日羅菩提》, 卷九,頁571中。
56.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十,《大正》卷51,頁932上。
| 頁175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伽觀法,[57]又說:「瑜伽觀法者,如前心地觀經及羂索經所說觀想即是,蓋南天密教特色,主在瑜伽觀法,後金剛頂宗,一謂瑜伽宗者,亦本於此。[58]
不空羂索的佛王傳統及佛王造像
不空羂索觀音的經典,自隋代的闍那崛多於開皇七年(587) 五月譯出《不空羂索咒經》之後,[59]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便都具有「伊尼鹿彩覆其肩」,即「披黑鹿皮」,的造像特徵。所謂「披黑鹿皮」的造像特徵,就是見有一鹿頭垂挂在左肩上的造像特徵。闍那崛多所譯的《不空羂索咒經》如此說明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狀如摩醯首羅天,頭上髮悉如螯髻,方作華冠,肩上當畫作黑鹿皮覆在左肩上。」[60]玄奘於唐顯慶四年(659)五月於慈恩寺翻譯的《不空羂索神咒心經》,[61]在描述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時也說了相似的話:「似大自在天,頂有螯髻首冠花冠,翳泥耶皮被左肩上,自餘身份瓔珞環釧而為莊嚴。」[62]
長壽二年武則天共敕譯了三部不空羂索觀音的經典。此三部不空羂索觀音的經典即是,慧智翻譯的《讚觀世音菩薩頌》、寶思惟翻譯的《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 及菩提流志翻譯的《不空羂索咒心經》一卷。[63]菩提流志所譯的《不空羂索咒心經》,在記述不空羂索觀音造像時,也與其他經典所記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一樣:「其身黃白紺髮垂下,首冠華冠,披翳泥耶皮如摩醯首羅狀。環釧皆以珍寶而嚴飾之。」[64]寶思惟所譯的《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不但稱不空羂索為「聖觀自在菩薩」,而且在造像上也有變化。該經如此記聖觀自在菩薩的造像:
57. 大村西崖,《密教發達志》,上卷,頁328。
58. 同上,頁328。
59. 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沙門闍那崛多譯經錄》,卷七,《大正》卷55,頁548下。
60. 隋天竺沙門者那崛多譯,《不空羂索咒經》,頁402上。
61.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不空羂索神心經》,〈不空羂索咒心經後序〉,頁406上。
62. 同上,《不空羂索神心經》,頁405上。
63. 見《開元錄•沙門釋慧智》,卷九,《大正》卷55,頁565下;《開元錄•沙門阿儞真那》,卷九,頁566下;《開元錄•菩提流志》,卷九,頁569下。
64. 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不空羂索咒心經》,頁409上。
| 頁176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其身黃白,首戴華冠,紺髮分被兩肩前後,慈顏和悅,放百千光,清淨殊勝,面有三目,以純白綖交絡肩臆,以翳泥耶鹿王皮而覆肩上。莊飾寶帶以繫其腰,尊者四臂,左邊上手執持蓮花,下手執持澡瓶,右邊上手施無畏手,下手執數珠,皆以珍寶嚴飾之,身著天衣立蓮華上。有大威德瓔珞短長,交髆垂下耳璫臂印,及以環釧皆寶飾之。頂上畫作無量壽佛,於其幀內畫種種華。[65]
不空羂索觀音似乎在七世紀末期之後便有「聖觀自在」或「聖觀音」之稱,且在造像上出現多臂的形象。其所持的物件,除了常見的蓮花、澡瓶之外,多了數珠等。北天竺婆羅門大首領李無諂在久視元年(700) 譯出《不空羂索陀羅尼經》,此《經》所記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法也是三眼四臂,四臂所持的物件及手印都與寶思惟所譯的《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一樣,披黑鹿皮。[66]
多臂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並不止于四臂。菩提流志于神龍三年(707) 所譯的《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67]便提到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有:一面二臂、一面四臂、三面四臂、三面六臂、三面十臂、一面三目一十八臂、十一面三十二臂等不同的造像法。[68]
無論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如何變化,到了不空來華發展金剛頂教法的時代,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基本上只有手臂及面上的變化。譬如,不空翻譯的《佛說不空羂索陀羅尼儀軌經》說:「如圖畫不空羂索觀世音菩薩,如大自在天,首戴寶冠,冠上有化阿彌陀佛,被鹿皮,衣七寶衣服,珠瓔環釧種種莊嚴,執持器杖。」[69]
不空羂索觀音的信仰在摩醯首羅或天王信仰盛行的南天出現,并用摩醯首羅的造像法,這說明不空羂索觀音的信仰,乃衍自南天的摩醯首羅信仰或天王傳統的信仰。不空羂索觀音造像法用摩醯首羅造像法的現象,可以說是「摩醯首羅觀音化」的現象。此「摩醯首羅觀音化」的結果,就是產生不空
65. 唐天竺三藏寶思惟奉詔譯,《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卷上,《大正》卷20,頁422中。
66. 北天竺婆羅門大首領李無諂譯,《不空羂索陀羅尼經》及《經序》,《大正》卷20,頁409中及頁410下。
67. 《開元錄•沙門菩提流志》,卷九,頁569中。
68. 大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譯,《 羂索神變真言經》,《大正》卷20,頁227-398。
69. 師子國三藏阿目佉(不空)奉詔譯,《佛說不空羂索陀羅尼儀軌經》,卷上,頁436下。
| 頁177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羂索觀音佛王傳統的信仰。摩醯首羅原是密教天王傳統的天王,在摩醯首羅被密教觀音化之後,密教不空羂索觀音即取代了天王摩醯首羅的天王地位,並成為觀音佛王傳統中的「佛王」(Buddharaja)。此處所謂的「佛王」, 即是「不空羂索觀音即是王」或「王即是不空羂索觀音」的意思。這就是金剛頂的「金輪佛頂」的信仰來源。
不空羂索的造像法使用印度教摩醯首羅的造像法之後,南天的觀音佛王造像及天王造像必有混淆不清的現象。事實上,不然。不空羂索觀音佛王的造像,因在「頂上畫作無量壽佛」的緣故,還是能區分佛教與印度教之別。
金剛頂在南天摩賴耶成立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對金剛頂的發展而言,乃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的出現,不但使金剛頂的信仰具有實際的使用價值,能作為帝王治國的意識形態,而且也使金剛頂的發展,因為帝王的使用而廣傳至印度以外的亞洲各地。中國最早翻譯不空羂索觀音經典的年代是在隋代或第六世紀的末期,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因此可以推溯至第六世紀的末期或更早。雖是如此,此觀音佛王信仰真正成為南天、中國及南海諸國流行的佛教治國意識形態,乃在第七世紀之後的事。
南海諸國七世紀之後發展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的情形
印尼於何時傳入此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我們不很清楚。不過印尼使用此佛王傳統的時間非常長,一直到十三世紀或更久,還有印尼帝王使用此佛王傳統治世。印尼雅加答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Indonesia, Jakarta) 收藏有一尊1286年所造的八臂不空羂索觀音的巨型立像。據說此像乃是爪哇王維斯瓦如帕庫馬拉(Javanese King Visvarūpakumāra) 以統治者的身分送給當時蘇門答拉王朝(Sumatran kingdom)的禮物。耶地•色地雅瓦提(Edi Sedyawati) 說,此尊八臂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有爪哇王維斯瓦如帕庫馬拉的相貌特徵。[70]此像之所以會被認為是爪哇王維斯瓦如帕庫馬拉的造像不是沒有原因。除了此像有該王的相貌特徵之外,雕有造像記的基座上方,也雕有一排佛教轉輪王的隨身七寶:馬寶、金輪寶、玉女寶、神珠寶、大臣寶、
70. Haryati Soebadio, ed., Art of Indonesia, Archipelago Press, 1997, p. 71. 爪哇王維斯瓦如帕庫馬拉之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
| 頁178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兵寶及象寶。這說明此像乃是一位佛教轉輪王以不空羂索觀音面貌面世的佛王造像。此像既是爪哇王維斯瓦如帕庫馬拉的轉輪王像或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像,這就說明維斯瓦如帕庫馬拉在統治爪哇時期,乃是使用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治世。
比這尊收藏在雅加答國立博物館稍早的一尊爪哇王所造的不空羂索觀音立像,乃見於東爪哇馬朗(Malang)地區的加哥遺址(Candi Jago)。此像的造像記說, 此像乃是為新加薩利王朝(Singasāri dynasty)的維斯奴瓦答那王(King Wisnuwardhanā, died 1268)所造。[71]此像很顯然的也是一尊維斯奴瓦答那王以不空羂索佛王面貌面世的造像。由此像,我們也知道,東爪哇的維斯奴瓦答那王必以不空羂索佛王傳統治國。
目前所能追溯的最早期之印尼不空羂索觀音佛王造像,都是造在七、八世紀之間,與武則天發展此傳統的時間相近。譬如,羅伯。基本尼斯(Robert Kipness)所收藏的一尊在印尼蘇門答拉(Sumatra)出土的七至八世紀的銅雕不空羂索觀音立像就是一個例子。[72]在中爪哇婆羅婆多遺址的《入法界品》造像中也見有不空羂索的造像。約翰。密細將此像視為該址《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六臂觀音菩薩造像。[73]約翰。密細並不知道此六臂觀音像是尊不空羂索觀音的坐像。此六臂觀音的造像,目前保存的情形還依稀可辨:觀音頭冠的坐佛已無頭,但可辨認為一坐佛。臉部的造像尚清晰,但頸部至胸前的飾物全毀。兩臂所持或所作的手印已不能分辨,但其他四臂的所持的物件及手印尚可辨認:左下持澡瓶,左上持蓮花,右上持數珠,右下施無畏印。[74]就此四臂所持的物件及手印來判斷,此觀音確實是第八世紀所流行的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婆羅婆多此尊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是不是建造此址的山帝王的造像?由于文獻不足,我們無法確認。
烏荼版《華嚴經•入法界品》所記的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只有二臂,[75]但此址的觀音造像卻有六臂,這說明此時代,甚至之後,的印尼帝王都喜歡將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像造成多臂的形象。
南海除了古代的印尼有施行不空羂索佛王傳統的歷史之外,古代的泰國
71. R. Soekmono, 「Indonesian Architecture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a Brief Survey」, Jan Fontein, The Sculpture of Indonesia,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at Washington, 1990, p. 82.
72. Nandana Chutiwangs and Denise Patry Leidy, Buddha of the Future, p. 49, plate 26.
73. John Miksic, Borobudur, Golden Tales of the Buddhas, p. 133.
74. Ibid., 約翰、密細認為,此觀音的右下手乃施「施印」(charity mudra).
75. 見後詳述。
| 頁179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與柬埔寨亦有施行此傳統的痕跡。泰國第七世紀至第十世紀在柴亞地方 (Chaiya district)便造有多尊不空羂索觀音的石雕立像。這些不空羂索石雕立像,都呈二臂,且左肩都披有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特徵,即披黑鹿皮的造像特徵。[76]就造像上來判斷,泰國柴亞出土的這些不空羂索觀音佛王的造像,要比在婆羅婆多所見的六臂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要早。
古代柬埔寨施行密教不空羂索佛王傳統最具體的例子就是闍邪跋摩第七(Jayavarman VII, 1181-ca1218)施行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治世的例子。謝得士在提到闍邪跋摩第七所建的吳哥佛教遺址(Angkor Thom)的造像時說:在吳哥佛教遺址最中央的寺院遺址巴雍(the Bayon or the central temple of Angkor Thom), 我們見不到代表「天王」的神物「林噶」(Linga,濕婆的生殖器)立于此建築物的中央,反而見到一座巨型的石雕「佛王」(Buddharaja) 造像。此雕像不但是一尊濕婆教天王(the Sivaite Devaraja)造像的代替品,而且也是一尊奠此基業的帝王之神化雕像。此王的造像亦見造于此遺址之每個塔形的上部,呈四面面向四方之「普門世間主菩薩」(Bodhisttva Lokeśvara Samantamukha)的造像型式。[77]
珍•玻以色利爾(Jean Boisselier)認為,這些四面面向四方的「普門世間主菩薩」的造像,原是金剛神(Vajrapani)的造像,此些造像被世間主(Lokeśvara)作為轉法輪之用。[78]
在巴雍塔形建築物上所見的四面面向四方的「普門世間主菩薩」的造像,並不是珍•玻以色利爾所言的「金剛神」的造像,而是具有摩醯首羅天王造像特徵的密教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
元魏釋曇曜的《大吉義神咒經》卷一即提到,摩醯首羅天王也具有「四道面」之名或「四面面向四方」的造像特徵:
復告四道面天王有大名稱,住凈居天阿那含處,名摩醯首羅,及其眷屬輔相大臣,汝等宜應擁護此咒。[79]
76. Nandana Chutiwangs and Denise Patry Leidy, Buddha of the Future, p. 79, plate 45. See also, Piriya Krairiksh, Art in Peninsular Thailand Prior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 D., Bangkok: The Fine Arts Department, 1980, p. 159.
77. G. Coedes, Walter F. Vella (ed.), Susan Brown Cowing (tra.),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p. 175.
78. Ibid.
79. 元魏昭玄統沙門曇曜譯,《大吉義神咒經》,卷一,《大正》卷21,頁570。
| 頁180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在柬埔寨吳哥巴雍遺址所見的「四面面向四方」的「普門世間主菩薩」的造像,由「普門世間主菩薩」之名來判斷,此名即有指謂「觀世音菩薩是世間主」的意思。所謂「世間主」,指的就是「統四邊畔」的轉輪王、天王或佛王。因,《法華經。普門品》即稱觀世音菩薩為「普門菩薩」(Bodisattva Samantamukha)。[80]故此「普門世間主菩薩」,就有指「觀世音菩薩為世間主」或「觀音佛王」的意思。
在密教觀音佛王傳統中,只有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法與天王摩醯首羅天王的造像法相疊。因此,《大吉義神咒經》所記的摩醯首羅天王的「四道面」造像法亦能成為不空羂索觀音佛王的造像法。
事實上,初唐菩提流志所譯的《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已載有 「四面大悲觀音」因持「不空陀羅尼」,具不空羂索觀音的性能及成就之說,[81]故此「四面大悲觀音」亦能有 「不空羂索觀音」之稱。
種種證據都能說明,闍邪跋摩第七的「四面面向四方」的「普門世間主菩薩」的造像,就是其不空羂索觀音佛王的造像。
謝得士雖然認為造在巴雍佛教遺址各塔上的「四面面向四方」的「普門世間主菩薩」的造像亦是闍邪跋摩第七的造像,然他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在遺址上的這些「普門世間主菩薩」的造像,為何都被造成「四面面向四方」的造像型式。謝得士之所以會無法說明這些像被造成「四面面向四方」的原因,與他不知道古代柬埔寨所尊崇的摩醯首羅天有「四道面」之稱有關之外,與他不知道東南亞流行的不空羂索觀音佛王造像能使用摩醯首羅像造像此事也有關系。
吳哥巴雍佛教遺址上的這許多「普門世間主菩薩」的造像,因此是古代柬埔寨王施行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最好的證據。事實上在吳哥遺址附近的新瑞(Siem Reap)也出土過791年立觀音像的銘文,[82]這說明吳哥地區有施行觀音佛王傳統,推崇觀音信仰的現象。
古代南海各國及中國自第七、八世紀之後頻繁施行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治國的情形即說明了,此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自由南天傳出之後,便一直受到亞洲各地帝王的青睞。這些南海諸國及中國的帝王,在使用此傳統治國之際,都有自己喜好的不空羂索佛王造像法。雖是如此,無論這些帝王如
80. 見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花經•觀世音普門品》,卷七,《大正》卷9,頁56下-58。
81. 唐菩提流志譯,《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三,頁243上。
82. Ibid., p. 94.
| 頁181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何造自己的不空羂索佛王造像,其等所使用的造像法,基本上都還是依照金剛頂經典所記的不空羂索造像法而造其等的造像。
密教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自第六世紀末期出現於歷史舞台之後,最遲在第七世紀的初期必傳至鄰近的烏荼。到了烏荼王進獻《華嚴經》的時代,烏荼已是南天非常重要的不空羂索觀音信仰地。這就是為何在古代的烏荼國遺址出土有巨型的觀音造像的原因。因此,烏荼的密教發展,不會如德巴拉。密特拉所說,烏荼的大乘佛教在第九世紀中期左右才逐漸形成密教化或金剛乘(Vajrayana)化。[83]
烏荼王所進獻的《華嚴經》版本
第八世紀末烏荼王所獻的《華嚴經》,事實上只有《入法界品》(Gaṇḍavyūha)的經文內容,而此《入法界品》的名字,照釋般若翻譯的《華嚴經》之〈出經後記〉的說法,也稱為《普賢行願品》。有關此《華嚴經》經文在唐代翻譯的經過,上述的 〈出經後記〉有如此的記載:「貞元十一年 (795) 十一月十八日進奉梵夾,十二年(796) 六月五日罽賓三藏般若等人奉詔于長安崇福寺翻譯,十四年(798)二月二十四日全經譯畢。[84]「貞元」是唐德宗的年號,因此,當時南天竺烏荼王是將《華嚴經》進獻給大唐皇帝唐德宗。
烏荼王進獻《華嚴經》的事,亦見記于《釋般若傳》及《釋蓮花傳》等文獻,[85]譬如,《宋高僧傳。釋蓮花傳》即說,南天竺烏荼國王書獻支那天子的《華嚴經》梵夾,乃是中印度僧人釋蓮花以信者的身分附舶將來。釋蓮花帶來烏荼版《華嚴經》的事有一段因緣。該《傳》說:
釋蓮花本中印度人,以興元元年杖錫謁德宗,乞鐘一口歸天竺聲擊。敕廣州節度使李復修鼓鑄畢令送於南天金堆寺。華乃將此鐘於寶軍國毗盧遮那塔所安置。後以華嚴經後分附舶來為信者。般若三藏於崇福寺翻成四十卷
83. Debala Mitra, Bronzes from Achutrajpur ., p. 17.
84. 同上。
85. 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釋般若傳》及《宋高僧傳•釋蓮花傳》,《大正》卷50,卷三,頁722及頁721。
| 頁182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焉。一云梵夾本是南天烏荼國王書獻支那天子。書云: 手自書寫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五十五聖者,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謹奉進上。[86]
南天烏荼王之所以會進獻《華嚴經》,大概就是因為唐德宗在興元年間(784)曾送烏荼王一口鐘。烏荼王為了感謝德宗送鐘之誼,故有進獻《華嚴經》之事。《釋蓮花傳》所言的「寶軍國」,應該就是當時烏荼國的國名,也是學者所言的包馬•卡拉王國的中文名字。這就是烏荼版《華嚴經》有四十卷《華嚴經》之名的來源。《貞元錄•釋般若傳》對烏荼王所獻的《華嚴經》也有一些說明。該《傳》說:「梵本大方廣佛花嚴經總有六夾,共有三萬偈,大唐已譯八十卷,當第二夾了。今南天竺國王所進當第三夾,有一萬六千七百偈。右件經當舊譯八十卷花嚴經第九會,在室羅伐城說。罽賓三藏沙門般若宣梵文,翰林供奉光宅寺沙門智真譯語,西明寺翻譯經沙門圓照筆受……與舊花嚴經第九會入法界品同譯……」[87]
照《釋般若傳》的說法,烏荼王所獻的《華嚴經》 (或《花嚴經》), 乃是「第三夾」。此處所言的「第三夾」, 應指第三個版本。木村清孝將《華嚴經》分為四個版本,即(1) 東晉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所譯的六十卷《華嚴經》, (2)唐代實叉難陀(Śikṣānanda)所譯的八十卷《華嚴經》,(3) 唐代釋般若 (Prajñā)所譯的四十卷《華嚴經》,及 (4) 耆那密特拉 (Jinamitra)於九世紀末所譯的藏本《華嚴經》。釋般若所譯的《華嚴經》, 乃相當於其他三版本的最後一章《入法界品》。[88]
中國最早的《華嚴經•入法界品》之譯本,并不是唐代釋般若所譯的南天烏荼本,而是東晉支法領自于闐取來的梵本。[89]此本即是於義熙十四年(418)三月十日在道場寺為佛陀跋陀羅 (覺賢)始譯,元熙二年(420)六月十日畢譯的六十卷《華嚴經》。[90]此後,乞伏秦沙門釋聖堅又譯出《羅摩伽經》三卷,即《華嚴經。入法界品》的異譯。[91]唐武則天代天竺三藏地婆訶羅也譯出《大
86. 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釋蓮花傳》,卷三,頁721中。
87. 唐圓照撰,《貞元錄•釋般若傳》,卷十七,《大正》卷55,頁894下-895中。
88. 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 東大圖書公司, 1996, 頁1-2。
89. 支法領乃受其師廬山慧遠之命與法凈自于闐的遮拘槃國取來此本。見海東新羅國崔致遠結,《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第五科,《大正》卷50,頁281下。
90. 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三,〈沙門佛陀跋陀羅譯經錄〉,《大正》卷55,頁505中。
91. 智昇撰,《開元錄》,卷十一,頁590下。
| 頁183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92]繼之,于闐沙門實叉難陀於武氏聖曆二年(699)十月八日譯出的八十卷《華嚴經》,也是由于闐取來的版本。[93]釋般若所譯的《華嚴經•入法界品》,在中國當時至少已經是第五譯了。
《華嚴經•入法界品》的出經地點
筆者在拙作〈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一文中,因見佛陀跋陀羅及實叉難陀等所譯的《華嚴經•入法界品》皆傳自中亞于闐(Khotan),且古代的于闐王也有推崇《華嚴經》及使用《華嚴經•入法界品》做佛王的現象,因此認為,《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可能是在中亞于闐出經。[94]筆者這種想法,當然只是一種推測。
許多學者因見《華嚴經•入法界品》記有許多與南印度地方有關的地名,因此不是認為《華嚴經。入法界品》是以南印度為背景而成立之經典,[95]便是認為《華嚴經•入法界品》最先是在南印度流傳,或甚至是在南印度制作的經典。譬如,呂澂在其《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引日本學者高峰了洲之《華嚴思想史》說:
在印度,華嚴一類經典是當公元第二世紀中頃先流行于南方的。這只要看經文的重要部分《入法界品》以福城做根據地,並提到當地的大塔,便可暸然。福城即是東南印濱海地馱那羯磔迦城,大塔又就是阿摩羅跋提塔,各有實地實物可考。而從現存大塔的欄柱銘題上看,塔建于公元一三0年以後,提到它的《入法界品》當然更要遲出了(參照高峰了洲《華嚴思想史》九-十三頁)。[96]
印順法師在《龍樹龍宮取經考》一文中,用龍樹 (Nagārjuna)入龍宮取《華嚴經》 的文獻如,《龍樹菩薩傳》、《付法藏因緣傳》、《凈名經玄論》、《大
92. 同上。
93. 同上,《開元錄》,卷九,〈沙門實叉難陀譯經錄〉,頁565下。
94. 見拙作,〈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國學研究》,第七期, 頁269-311。
95. 中村元,《華嚴經の思想史的意義》,《華嚴思想》,1960,法藏館, 頁81-144;並見木村清孝,李惠英譯,《中國華嚴經思想史》,頁15。
96.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頁391。
| 頁184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唐西域記》等,及其他的佛教文獻如,《華嚴經•入法界品》及《華嚴經傳記》等,對《華嚴經》《入法界品》的出經地點,即其認為的,《入法界品》所記的文殊師利(Mañjuśrī)到南方弘化的起點「福東城」,作了一些考證工作。印順法師認為,「在今 Orissa(奧里薩,即烏荼)的 Jajpur 市東北,約二十里處,有名為 Bhadraka 的,與福城的語音及方位,無不恰合。」[97]「烏荼」之所以被印順法師認為是《入法界品》的出經處,除了他認為,《入法界品》所記之地名與玄奘在《西域記》中所記的地名都吻合,有地理根據之外,他也用第八世紀中國的佛教文獻如,「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烏荼國王手寫《華嚴經》《入法界品》,呈獻中國」及「日照三藏《華嚴經傳記》說:南天竺國,近占波(Campa,佛世央伽首都),有一僧伽藍,名毗瑟奴(可能補澀波的別傳)……有一大乘法師持華嚴經一帙來至其寺……華嚴一經,盛于此國」之事,[98]來證明此事。
印順法師在此文中,不僅有將《入法界品》出經的地點視為南印度的「烏荼」,同時也將龍樹在龍宮取《華嚴經》的傳說地點視為烏荼。[99]龍樹在龍宮取摩訶衍經論的傳說,記載於許多佛教文獻,譬如,印順法師所引的《龍樹菩薩傳》便說:
……大龍菩薩見其(龍樹)如是,惜而愍之,即接入海,於宮殿中開七寶藏,發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龍樹受讀九十日中通解甚多……龍樹既得諸經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還送出於南天竺,大弘佛法,摧伏外道,廣明摩訶衍,作優波提舍十萬偈,又作莊嚴佛道論五千偈,大慈方便論五千偈,中論五百偈,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又造無畏論十萬偈,中論出其中。[100]
《付法藏因緣傳》也提到同樣的故事。[101]然此兩文獻都沒有提到龍樹在龍宮取《華嚴經》的事,但印順法師卻認為,「龍樹從龍宮所得的經典,主
97. 釋印順,《龍樹龍宮取經考》,收入釋印順,《佛教史地考論》,《妙雲集》,下編之九,正聞出版社, 1990 (14版),頁217。
98. 同上,頁219。
99. 同上,頁212-215。
100. 姚秦鳩摩羅什譯,《龍樹菩薩傳》,《大正》卷50,頁184下。
101.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五,《大正》卷50,頁318中。
| 頁185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要為《華嚴經》。」[102]大乘佛教常以非常隱諱的態度處理大乘經典出經的情形。我們俄而會在佛教經典或佛教文獻中見到大乘作者說, 由「結集」(Buddhist council)出大乘經、律、論。雖是如此,這些提到由「結集」出大乘經、律、論的作品,基本上都沒有進一步的告訴我們大乘如何利用「結集」造經,且造了那些經。譬如《蓮花面經》便是一部提到大乘如何用「十二部經」,即大乘造經法,[103]在罽賓造大乘經典的大乘作品。此經雖然提到「彼諸阿羅漢結集如來十二部經,廣造諸論,彼罽賓國猶如帝釋歡喜之園」,也提到當時參與造經的有「頗羅墮逝賓頭樓等」,[104]然到底此次的大乘「結集」造了那些大乘經,《蓮花面經》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同樣的情形也見於《婆藪槃豆法師傳》。由《婆藪槃豆法師傳》,我們知道,大乘又於罽賓召開一次「結集」。此次罽賓結集共有五百阿羅漢及五百菩薩參與造經論的活動,並經十二年的時間,最後經馬鳴(Aśvaghosa)表文句,才結束此次的結集。[105]《婆藪槃豆法師傳》是一部對此次結集情形有比較詳細說明的作品。此《傳》雖稱此次結集所造的論是薩婆多部( the Sarvāstivāda)的「阿毗達摩」Abhidharma),[106]然從整部《傳》所要說明的內容是無著(Asaṅga)或世親(Vasubandhu)得大乘經及造大乘論的情形來判斷,筆者認為,本《傳》所言的結集,也是一次大乘的結集。造《傳》者認為此次的結集是一次「薩婆多部」結集的原因,乃因主持結集的僧人如,迦旃延子等,皆出於薩婆多部之故。[107]
《婆藪槃豆法師傳》 所記的結集,是後貴霜迦膩色迦王(King Kaniska of the Later Kushan, 187-244)時代所召開的結集。[108]此次的結集會記載於《婆藪槃豆法師傳》中,說明《傳》中所言的「北天竺富婁沙富羅(Purushapura)人」「婆藪槃豆」(Vasubhadu)或「阿僧伽」 (Asaṅga,也譯為『無著』),必有參與此次結集的活動,否則此次結集的事不會無端的出現於無著的《傳》中。
102. 釋印順,《龍樹龍宮取經考》,頁215。
103. 見拙作,《大乘佛教的造經方法與早期佛教文學及藝術的發展關系》,《嶺南學報》,第一期 (1999),頁137-164。
104.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蓮花面經》,卷下,《大正》卷24,頁1075中。
105. 陳真諦三藏法師譯,《婆藪槃豆法師傳》,《大正》卷50,頁189。
106. 同上。
107. 有關次結集的事,筆者在拙作《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已有詳細的說明。見拙作,《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第七章,第一節〈迦膩色迦王的大乘佛教結集活動〉,頁485-534。
108. 同上。
| 頁186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此《傳》除了提到結集的事之外,也提到無著「數上彌勒兜率多天諮問大乘經義,彌勒廣為解說,隨有所得,還閻浮提,以己所聞為餘人說」之事。[109]無著在兜率多天(Tuṣita Heaven)所聽聞的大乘經,照該《傳》的說法,有「佛昔所說華嚴經等諸大乘經悉解義。」[110]
《婆藪槃豆法師傳》所記的無著上兜率多天取大乘經之事,與我們在《龍樹菩薩傳》所見到的龍樹入龍宮取經的故事一樣具「神化性」。這說明,記載大乘佛教造經論的作品,都有故意要「神化」或「模糊」大乘出經的確實情形。因此,筆者認為,無著上兜率多天取大乘經或龍樹入龍宮取大乘經論的說法皆不能信。
照《付法藏因緣傳》的說法,龍樹乃是馬鳴及無著之後的人物,[111]如果此文獻所記無誤,《華嚴經》早在無著的時代已在罽賓或北印度出經。這大概就是《龍樹菩薩傳》及《付法藏因緣傳》沒有提到龍樹於南印度出《華嚴經》的原因。既是如此,《華嚴經》應在北印度出經,而不是在烏荼出經。
到底《入法界品》是不是在烏荼出經?參預烏荼版《華嚴經》翻譯工作的釋圓照,[112]在其所撰的《貞元錄。釋般若傳》中即提到,「右件經當舊譯八十卷花嚴經第九會,在室羅伐城說」。此話的意思就是說,《入法界品》的經文出經地點是在「室羅伐城。」 「室羅伐城」(Śrāvastī), 也稱為「舍衛國城」。丁福保在其《佛教大詞典》中引《大唐西域記》說, 「舍衛城」在「中印度土境」,「是勝軍大王所治國都也。」[113]唐代既有《入法界品》出自中印度「舍衛城」之說,《入法界品》最早在南天流傳或出自南天烏荼的說法便有商榷的餘地。
古代中印度成為《華嚴經》,甚至《入法界品》的發展中心,在中國第五世紀之後的佛教文獻也有諸多記載。
第五世紀之後中印度《華嚴經》的傳播情形
109. 陳真諦譯,《婆藪槃豆法師傳》,頁188下。
110. 同上。
111.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五及卷六,頁314-318。
112. 罽賓三藏般若奉詔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出經後記〉,《大正》卷10,頁848下,「 罽賓三藏賜紫沙門般若宣梵文,東都天宮寺沙門廣濟譯語,西明寺賜紫沙門圓照筆受……」
113. 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詞典》,中冊,宏願出版社,1995,頁1524,〈舍衛城條〉。
| 頁187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東晉慧遠的弟子支法領及法凈,在于闐遮拘槃國取回來的《華嚴經》,便是中國六十卷《華嚴經》最早的全部譯文根據,[114]此經在元熙二年(420)被佛陀跋陀羅等於南宋譯出之後不久,由北印度及中印度取中國南方海上絲線來華的兩位南宋時代的重要僧人,求那跋摩(Guṇavarman)及求那跋陀羅(Guṇabhadra),也都在宋都講過《華嚴經》。此二印度僧人來華所取的海上航線,都由古代的師子國坐船到闍婆(Java), 再由闍婆乘舶來華。《高僧傳•求那跋摩傳》說:
求那跋摩(Guṇavarman)本北印度罽賓王族。二十出家,年三十拒受王位遁跡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眾,咸謂已得初果。後至闍婆,助王弘化。元嘉元年(424) 九月,南宋沙門慧觀、慧聰等面啟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沖、道俊等往彼祈請,並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多加等,必希顧臨宋境。跋摩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元嘉八年達于京師建鄴。[115]
求那跋摩先以王師的姿態在闍婆發展佛教,後以王師或佛教專家的身份受宋文帝的邀請來華。因此,求那跋摩並不是一位普通的佛教僧人。求那跋摩在宋都除了譯出《菩薩善戒》等戒之外,也「開講法華及十地(華嚴)」。[116]此處所言的《十地》,乃是《華嚴經》的《十地品》。由此可知,求那跋摩在中國及闍婆都有傳播大乘佛教的活動,而其專長,則在于《法華》及《華嚴》二部。
從此文獻,我們不能確定求那跋摩的《華嚴》知識從何得來。但從另一位同時代由師子國輾轉來華的中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羅在中印度接觸《華嚴經》的經驗,我們即知,第五世紀初期的中印度就有發展《華嚴經》的現象。[117]求那跋陀羅一定對《華嚴經》有特別的心得,因此在其居留南宋期間,便有譙王請其開講《華嚴經》的「神話」故事。《華嚴經傳記》說:
114. 見注90。
115. 梁釋慧皎撰,《高僧傳•求那跋摩傳》,卷三,《大正》卷50,頁340,簡述。
116. 同上,頁341上。
117. 《高僧傳•求那跋陀羅傳》說:求那跋陀羅「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嘆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見《高僧傳•求那跋陀羅傳》,卷三,《大正》卷50,頁344上。
| 頁188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譙王欲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嘆,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則備領宋言。於是遠近道俗,服其精感,請令就講。遂講華嚴,數十餘遍。[118]
求那跋陀羅在中國不但推廣如《華嚴經》之大乘教法,也十分賣力地提倡密教觀音信仰。這說明,第五世紀初期開始中印度也有發展密教觀音信仰的現象,而中國南方密教觀音信仰的興起,與之推廣不無關系。
第六世紀初期(508),另一位中印度僧人勒那摩提也到洛陽來翻譯《華嚴經》的《十地論》等。其在北魏期間,北魏皇帝宣武帝「每令講華嚴經」。[119]
第五世紀初期之後,由于中國南方海上交通網的發達,中印度僧人不但有借海上交通來到中國傳播《華嚴經》的情形,而且也有將《華嚴經》傳入南海諸國的現象。《續高僧傳•拘那羅陀傳》說,拘那羅陀,譯云真諦,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梁武帝大同中敕直後張范等送扶南獻使還國,乃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彼國乃屈真諦并齎經論,以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達於南海。[120]第六世紀初期,中國梁武帝對當時扶南發展佛教的情形非常暸解。天監五年(506),他在楊都壽光殿華林園已立有「扶南館」,用扶南僧人如,僧伽婆羅及曼陀羅等,為其翻譯佛經。[121]僧伽婆羅為梁武帝譯有《大育王經》等,並與曼陀羅也譯有《寶雲經》、《法界體性》及《文殊般若》三部合十一卷。[122]當時的扶南,必是南海一處大乘佛教發展的要地。因此他才會在敕直後張范等送扶南獻使還國之際,要求扶南國王送僧人及大乘諸經論來華。我們不知道文獻中所記的《法界體性》及《文殊般若》是否與《華嚴經》有關,但從梁武帝敕張范等請來《雜花經》一事,我們知道,第六世紀中期左右的扶南也有流通及發展《華嚴經》的現象。所謂的《雜花經》,
118. 見京兆崇福寺沙門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卷二,《大正》卷51,頁158中,並見《高僧傳•求那跋陀羅傳》,頁344中。
119. 《華嚴經傳記》,卷二,頁158下,并見《續高僧傳•菩提流支傳》,卷一,頁429上。
120. 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拘那羅陀傳》,卷一,《大正》卷50,頁429下,簡述。
121. 《續高僧傳•僧伽婆羅傳》,卷一,頁426上。
122. 同上。
| 頁189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即是《華嚴經》的異名。[123]
到了第七世紀,中印度還有發展《華嚴經》的記錄。中印度僧人地婆訶羅,或也稱日照,在武氏時代譯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124]當時中國的《華嚴》信仰也是相當盛行。華嚴宗賢首大師,即法藏,知道日照齎來「第八會文」,「遂與三藏校對」。[125]
日照來華所走的路線,必是取中印度橫切至古代占波(Champa,即今越南)再北上中國的這條南方絲路,因為日照來華之前曾到占波。這條由中印度到占波及中國的路線,與前面所談的自師子國經闍婆來華的海上路線不同。中印度到占波的走法,《續高僧傳•釋玄奘傳》有詳細的記述。《續高僧傳•釋玄奘傳》說:可以自那爛陀寺,即「瞻部洲中寺之最」,[126]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再東南行路經五國至三摩呾吒國,濱斥大海。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127]義凈所撰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在說明林邑與扶南的地理位置時說:「……南至占波,即是臨邑(林邑)。此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國,舊云扶南。先是裸國,人多事天,後乃佛法盛流。」[128]王邦維用伯希和之說,認為林邑的故地乃在今越南橫山以南的中部和南部地區,[129]而馮承鈞也認為,林邑的故地北界應在今日安南關所在之橫山,而南界則應尋漢之日南同秦之象郡的南界;林邑的最古都城,則應在廣南省中茶蕎廢址所在去尋。[130]印順法師將「占波」視為烏荼的說法,與事實相去太遠。
日照所述的占波發展《華嚴經》的始末情形如此:
至南天竺國,近占波城,有一僧伽藍,名毗瑟奴。於中有諸頭陀僧等,並小乘學。後忽有一大乘法師持華嚴經一帖來至其處。小乘諸師既不相
123. 見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下冊,台灣白馬精舍印, 1985,頁2825下。
124. 唐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大正》卷10,頁876-878。此卷經文乃是此《品》的第八會文。見《華嚴經傳記》,卷一,頁154下。
125. 《華嚴經傳記》,頁154下。
126. 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釋玄奘傳》,卷四,頁451下。
127. 同上,頁452上、中。
128. 翻經三藏沙門義凈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大正》卷54,頁205中。
129. 見義凈原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頁15-16。
130. 亦見馮承鈞,《占城史料補遺》,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商務印書館,1995,二編,頁129-30。
| 頁190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敬,彼大乘師乃留帖而去,不知所適。諸小乘學者,情盡不信,遂持此經帖投之井內。後數見井中光輝煥赫,上衝於外,有同烈火。以物鉤漉,果得華嚴。雖久在水中,都不霑濕。小乘學等,便信此經是佛所說,猶將不及小乘,遂置在小乘經律之下。及至明旦,輒見在上,訶諸群小,誰復輒移。對云:元無人動。乃還置下。明又如初……方知此經過於己學,以身投於地,宛轉號泣,懺謝迴心,專共授持。華嚴一經,盛於此國,諸小乘輩,舉宗歸敬,同深信焉。[131]
六、七世紀南海扶南及占波所發展的《華嚴經》,都是自中印度經海上傳入。中印度僧人向中國及南海所傳播的《華嚴經》,在第五世紀之後大概就以傳播《入法界品》為主。當時的中印度僧人為何要傳播《入法界品》?這不是沒有原因。《華嚴經•入法界品》出經之後,我們便在此經見到《華嚴經》佛王傳統的信仰基礎。《華嚴經》佛王傳統和上述所言的密教觀音佛王傳統的作用一樣,都是作為帝王治國的意識形態,只是兩者所信仰的神祗不同,前者常是彌勒,而後者則是觀音。
《華嚴經》佛王傳統的發展特徵
筆者在拙作〈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一文中已經說過,《華嚴經•入法界品》是我們見到《華嚴經》佛王傳統(the Avataṃsaka Buddharāja tradition)最始源的經典。在此《入法界品》中,我們不僅見到《華嚴經》的主佛毘盧遮那佛 (Buddha Vairocana)的過去身被視為轉輪王(cakravartin)身,[132]《入法界品》中所載的大菩薩如,彌勒菩薩(Bodhisattva Maitreya)、[133]普賢菩薩(Bodhisattva Samatabhadra),[134]及文殊師利菩薩(Bodhisattva Mañjuśri)的過去身也都被視為轉輪王身。[135]這種現象,說明這些佛、菩薩都在此《入法界品》中已被「佛王化」(Buddharajanized)。所謂「佛王化」,指的就是,「佛即是王,王即是佛」(He who is Buddha is rāja) 的意思。換言之,佛教的轉輪王能以佛或菩薩的面貌面世或統治其子民。佛教
131. 《華嚴經傳記》,卷五,頁170上。
132. 東晉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四,《大正》卷9,頁745下。
133. 同上,卷五十三, 頁732下。
134. 同上,卷五十四,頁739下。
135. 同上,卷五十七,頁764下。
| 頁191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轉輪王傳統的信仰內容及施行方法,在阿育王的時代已被制度化。雖是如此,佛教轉輪王傳統的信仰內容並不是一成不變。密教觀音佛王傳統及《華嚴經》佛王傳統在歷史上的出現,即說明了此轉輪王傳統已經被密教化。[136]
中亞的于闐王是不是最先使用《華嚴經》佛王傳統的治世者?由于文獻不足,我們不清楚。中亞及中國的帝王在使用《華嚴經》佛王傳統治世之際,除了都有尊崇《華嚴經》的現象之外,基本上也都以彌勒的佛王面貌面世,當然也有以毘盧遮那的面貌面世者。武則天在登位(690)之前,即敕中印度僧人日照(地婆訶羅)等於西太原寺歸寧院為其譯出《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等《華嚴經》,推崇《華嚴經》信仰。武氏登位之後,其便在流通天下的《大雲經疏》中說明自己就是《大雲經》中的女轉輪王出世及彌勒佛下生。武氏這種又是轉輪王又是彌勒佛的身份,就是彌勒佛王身。[137]既然《華嚴經》佛王傳統的發展與《入法界品》的信仰有關, 《入法界品》的傳播,便具有政治意義。
進獻《華嚴經》的烏荼王,也有發展《華嚴經》佛王傳統,推崇彌勒信仰的現象。《貞元錄》在說明烏荼王敬重大乘佛教的場合提到,當時的烏荼王乃以「法王」或「佛王」的姿態統治烏荼。該《錄》說:「自書寫乘航架海發使獻來,是知法王御曆不貴異貨珠珍,信重大乘以佛法僧而為上寶,斯乃拯拔淪溺,能證菩提。」[138]釋般若所譯的《華嚴經》之〈出經後記〉,也提到,烏荼王「伏願書此大乘經典進奉功德,慈氏如來成佛之時,龍華會上早得奉覲,大聖天王獲宿命智,瞻見便識,同受佛記,盡虛空遍法界,廣度未來一切眾生速得成佛。」[139]由此可知,當日的烏荼王確實在發展大乘佛教,並以「法王」及彌勒 (慈氏)佛王的姿態統治烏荼,提倡彌勒信仰。
南海之《華嚴經》彌勒佛王造像
開元四(716)年來長安,在中印度那爛陀求法的密教胎藏派僧人善無
136. 詳細內容請見拙作,〈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
137. 同上。
138. 西京西明寺沙門圓照撰,《貞元錄》卷十七,頁894中。
139. 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出經後記〉,頁848下。
| 頁192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畏,[140]在中國奉詔譯有兩卷彌勒菩薩瑜伽念誦法。此《念誦法》即是《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此《念誦法》所記的彌勒瑜伽修行法,與我們在上面所談論的金剛頂派瑜伽蓮花部的修行法一樣,都說能借修行瑜伽而達到「神、我同體」的境界。此種「神、我同體」的修行法,就是《華嚴經》佛王傳統及密教觀音佛王傳統的信仰基礎。因有此信仰基礎,或修行理論,轉輪王或法王便能以彌勒的面貌或觀音的面貌面世。《念誦法》如此記載慈氏菩薩的瑜伽修行法:「……是故我今禮愈誐/愈誐即是慈氏尊/是故我今修愈誐/速證慈氏同一體。」[141]
此《念誦法》也記有兩種慈氏(彌勒)的造像法。第一種造像法在此經中被提到多次,乃是兩臂慈氏的造像法:
其中圓明慈氏菩薩白肉色,頭戴五智如來冠,左手執紅蓮花,於蓮花上畫法界塔印,右手大姆指押火輪甲上,餘指散舒微屈風幢(說法之印),種種寶光,於寶蓮花上半跏而坐,種種瓔珞天衣,白帶鐶釧莊嚴。[142]
第二種的造像法,則是:「於蓮花上結跏趺坐,入三昧凝定,面貌慈軟,含笑具三十臂,各執寶蓮花,於蓮花上皆執本印契,各表三昧耶不同。有種種身光,頂背亦爾。初左第一手執蓮花,蓮花上畫法界塔印,右第一手執金剛拳……」[143]
這兩種慈氏菩薩的造像特色,都是在左手所執的蓮花上「畫法界塔印。」這種彌勒菩薩的造像法,與同時代不空所譯的《八大菩薩曼荼羅》之彌勒造像法不同。《八大菩薩曼荼羅》所記的慈氏菩薩造像法是:「想慈氏菩薩,金色身,左手執軍持,右手施無畏,冠中有窣堵波(塔),半跏坐。」[144]
善無畏的出身雖與南天烏荼有關,然在密教史上,學者一般都將之視為中印度胎藏派的密教僧人,[145]其所譯的《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可能就是中印度彌勒佛王信仰的「念誦法」及造像法。不空因是南天金剛頂派的
140. 宋贊寧撰,《宋高僧傳•釋善無畏》,卷二,《大正》卷50,頁715中。
141. 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善無畏奉詔譯,《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卷上,《大正》卷20,頁590上。
142. 同上,頁591上。
143. 同上,頁596。
144. 不空奉詔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大正》卷20,頁675中。
145. 宋贊寧等奉敕撰,《宋高僧傳•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大正》卷50,頁714-716。
| 頁193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密教高僧,[146]其所譯的《八大菩薩曼荼羅》,可能就是南天金剛頂之彌勒佛王的「曼陀羅」及造像法。
《華嚴經•入法界品》所記的彌勒佛王形象,乃是彌勒菩薩的形象。雖是如此,中國的《華嚴經》佛王造像,如武則天者,都是造成「倚坐」的彌勒佛像。[147]目前在南海諸國出土的七、八世紀所造的單尊彌勒造像,能依經辨別者,基本上都依不空所譯的《八大菩薩曼荼羅》 之「冠中有窣堵波(塔)」的彌勒菩薩造像法所造的像。這說明七、八世紀之後,在南天使用的彌勒菩薩造像法也被南海諸國的帝王使用來造其等的彌勒佛王造像。譬如,今日柬埔寨金邊藝術博物館 (the Phenom Penh Museum of Fine Arts),收藏有七世紀至十一世紀制作的多尊銅雕多臂彌勒菩薩造像。這些彌勒像,都是依金剛頂派「冠中有窣堵波」的慈氏菩薩造像法制作的彌勒像。其中一尊被定為八世紀至十一世紀,在 Wat Ampil Tok, Kompong Chhnang 出土的大型銅雕八臂彌勒菩薩立像,其冠中便造有窣堵波。
七、八世紀之際,此類彌勒菩薩像在古代柬埔寨地方似乎造得很多。麥德琳•季陶及丹尼爾•谷瑞 (Medeleine Giteau and Danielle Gueret )在其等所著的《高棉藝術-吳哥文明》一書中即收錄有,金邊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尊四臂銅雕彌勒菩薩立像及一尊八臂銅雕彌勒菩薩立像。此尊四臂的彌勒像,乃由暹邏(Siam)購入,不知出處,可能是吳哥王朝前(pre-Angkor)的作品。此尊八臂彌勒立像,因書中解說標題弄錯,不知是何時代及何地的作品。[148]
七、八世紀柬埔寨所造的單尊彌勒菩薩造像,因數量很多,且該地有施行「天王傳統」及「佛王傳統」的背景,[149]筆者因此認為此種彌勒菩薩的造像,應該就是金剛頂派在彼時制作《華嚴經》彌勒佛王造像的基本模式;特別是,柬埔寨自第六世紀之後便有成為東南亞《華嚴經》佛王傳統發展中心的史實。
我們在柬埔寨所見的銅雕彌勒菩薩造像,也見于東南亞其地區。譬如,在南達那•楚提旺 (Nandana Chutiwongs)與丹尼士•帕翠•萊地 (Danise Patry Leidy) 所著的《未來佛》(Buddha of the Future) 一書中,南達那•楚提旺
146. 同上,《宋高僧傳•唐京兆大興善寺釋不空傳》,頁712-714。
147. 見拙作,〈武則天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佛王形象〉。
148. Medeleine Giteau and Danielle Gueret, Khmer Art-The Civilizations of Angkor, France: ASA Editions/Somogy Editions d'Art, 1997, plate 100 and plate 101.
149. 參見拙作,《東南亞的「天王傳統」與後趙時代的「天王傳統」》,也見 George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chapter VII, pp. 97-133等處。
| 頁194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便提到,除了在柬埔寨見到此類的彌勒菩薩造像之外,在緬甸及泰國等地也都見有此類的彌勒菩薩造像,特別是泰國。[150]1964年在泰國中北部布利然省(Buriram)帕拉空•猜 (Prakhon Cai)的地方,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銅雕彌勒菩薩立像。楚提旺認為,泰國帕拉空•猜出土的銅雕彌勒立像,特別是「亞洲社會」(Asia Society)收藏的一批,在風格上,特別是臉部的特徵,很像柬埔寨吳哥王朝前(即九世紀之前)所造的彌勒菩薩像[151]。帕來空•猜並不是泰國唯一出土此類彌勒像者。南達那•楚提旺也提到泰國其他地方有出土此類的銅雕彌勒立像。[152]
雖然南達那•楚提旺也提到印尼有出土此類彌勒造像,然在其書中,她並沒有進一步引申說明。印尼施行《華嚴經》佛王傳統最有名的遺物,乃是中爪哇(Central Java)日惹((Yogyakarta)的婆羅婆多 (Borobudur)遺址。婆羅婆多遺址是山帝王朝(Śailendra kingdom)于760始建的一座像山型的巨型佛教遺址。照約翰•密細 的說法,此址共用460幅石雕雕塑《入法界品》之善財參師的故事。此460幅的《入法界品》的石雕,占此址2、3、4層的面積。其中334的石雕內容是善財童子參見彌勒菩薩、文殊菩薩及普賢菩薩的場面。在參見此三位菩薩的石雕造像中,善財到盧舍那「寶樓閣」(Virocana's Jewel Tower)見彌勒菩薩的故事,就占了遺址第三層走道兩側全部的石雕內容。[153]
善財見彌勒菩薩的經文,就是《入法界品》說明彌勒菩薩是位「佛王」的經文,也是《華嚴經》佛王傳統信仰彌勒為佛王的主要經文依據。第八世紀的山帝王朝將《華嚴經•入法界品》的經文內容,特別是彌勒佛王信仰的內容,雕在婆羅婆多,這當然是說明當時山帝王朝的帝王有特別推崇及使用《華嚴經》佛王傳統的現象。約翰•密細因注意到,婆羅婆多的《入法界品》石雕內容與烏荼版的《入法界品》之內容相近,因此他認為,烏荼版《入法界品》傳入爪哇的時間比中國更早。[154]
七、八世紀之後,南海諸國的帝王使用《華嚴經》佛王傳統治世的情形似乎也普遍,而這些帝王所使用的《華嚴經》佛王傳統,似乎都沒有以中印
150. Nandana Chutiwongs and Denise Patry Leidy, Buddha of the Future-An Early Maitreya From Thailand, p.26。 譬如,緬甸南部古代佛教遺址 Shrikshetra ,便見有此類彌勒菩薩銅雕立像。
151. Ibid., p.14 and cover pages, 1,4,5,8-9.
152. Ibid., pp. 34-35.
153. John Miksic, Borobudur-Golden Tales of the Buddhas, pp. 127-129.
154. Ibid., pp. 128-129.
| 頁195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度發展的《華嚴經》佛王信仰為根據,而都以南天金剛頂的信仰及造像法為依據。這很明顯的說明,七、八世紀之後,南天及南海都已經成為金剛頂的重要發展舞台。
烏荼版《入法界品》的特色
中天竺的《華嚴經•入法界品》在第五世紀之後傳入中國及南海諸國之際,一定也由中天竺傳入南天各地。傳入南天的《入法界品》,因南天密教金剛頂在南天的興起及發展,便被「金剛頂化」,而出現了金剛頂版的《入法界品》。「金剛頂化」的《入法界品》,即是烏荼版的《入法界品》。由于文獻有限,我們不知道,烏荼版的《入法界品》是在何時成立。但因其是烏荼王所進獻的版本,其很可能就是在烏荼改造的版本。
烏荼版《入法界品》,與初唐武則天時代及其之前所譯的《華嚴經•入法界品》的經文內容已有不同。特別在記述觀音信仰一節的經文里,烏荼版《入法界品》已具有七、八世紀烏荼密教觀音信仰的特色。東晉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羅所譯的《入法界品》,觀世音菩薩所居的地點及觀世音菩薩的形象與烏荼版《入法界品》所載的觀自在居所及形象很不一樣。
東晉版的《入法界品》說,觀世音菩薩乃居住在「光明山」的山西阿,「處處皆有流泉浴池,林木鬱茂,地草柔軟,結跏趺坐金剛寶座,無量菩薩恭敬圍繞。」[155]武則天於證聖元年(695)敕于闐僧人實叉難陀於東都大遍空寺始譯的八十卷《華嚴經•入法界品》,[156]雖已將觀自在的居所記為:「於此南方,有山名補呾洛迦」,然觀自在的形象尚不見如烏荼版如此「金剛頂化」。[157]這說明烏荼版《入法界品》 的確已受到南天金剛頂的改造。烏荼版《入法界品》的觀音形象,與七、八世紀南天信仰的不空羂索觀音形象,基本上沒有甚麼差別。這就是我們知道烏荼版《入法界品》在南天有被「金剛頂化」的原因。
釋般若翻譯的烏荼版《入法界品》,在用長行(sūtra)說明善財童子在南方觀自在菩薩所居之所補呾洛迦(Potalaka)問學觀自在菩薩如何修行菩薩
155. 東晉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一,《大正》卷9,頁718上。
156. 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奉制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十八,《大正》卷10,頁366-367。
157. 同上,頁366下。
| 頁196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道之後,便補入二段用偈頌(gāthā)體書寫的經文。[158]這兩段用偈頌體書寫的經文,皆不見記於早期的中譯《入法界品》。第一段用偈頌體書寫的經文內容,基本上與《法華經•普門品》所記的觀世音菩薩行善權方便 (upāyakauśalya)救度世間各種苦難的經文內容一致。[159]第二段用偈頌體書寫的經文,除了一部分用來描述觀自在的莊嚴形象 (image)之外,其餘的內容也是描述觀自在菩薩以「大悲菩薩」的形象救度世間苦難的經文。
此段描述觀自在形象的經文,與武則天於長壽二年(693)敕慧智翻譯的《讚觀世音菩薩頌》所述的不空羂索觀音形象的經文差不多完全一致。為了討論上的方便,筆者在此便要將此二經所記的觀世音形象的經文引述於下:
烏荼版《入法界品》如此記觀自在的形象:
種種華鬘以嚴飾/頂上真金妙寶冠/光明凈妙過諸天/威德尊嚴超世主/圓光狀彼流虹遶/外相明如凈月輪/頂相豐起若須彌/端嚴正坐如初日/腰繫金條色微妙/現殊勝相放光明/伊尼鹿皮作下帬/[160]能令者生歡喜/妙身種種莊嚴相/眾寶所集如山王/腰垂上妙清淨衣/如雲普現無邊色/真珠三道為交絡/猶如世主妙嚴身/……以白瓔珞為嚴飾/如白龍王環遶身/世主手執妙蓮花/色如上妙真金聚/毘琉璃寶以為莖/……[161]
《讚觀世音菩薩頌》則如此記:
尊重首飾甚嚴好/冠以曼陀及金花/虹蜺美麗以莊嚴/復如半月映山王/又似百寶成須彌/尊者身相甚微妙/猶如輕雨籠寶岳/伊尼鹿彩覆其肩/光明晃朗普周遍/巍巍挺特若金山/亦如滿月處虛空/又似薝波迦花色/勝彼摩醯首羅身/徒以白龍為瓔珞/右手執持金蓮花/毘琉璃寶以為莖/……[162]
158. 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六,《大正》卷10,頁733-735。
159.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花經•觀世音普門品》,頁56-58。
160. 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六,頁735上。該經的注2,認為此字應為「裙」字。但從目前記有此「伊尼鹿皮作下帬」的經文,都將此字記為「垂」字。
161. 同上,頁735上。
162. 唐天后代佛授記寺翻經沙門慧智制譯,《讚觀世音菩薩頌》,頁67中。
| 頁197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這兩段經文所記的觀世音形象,都有「頂上真金妙寶冠」,「伊尼鹿彩覆其肩」,「徒以白龍為瓔珞」,「右手執持金蓮花」等的造像特徵。在這些造像特徵中,因都有「伊尼鹿彩覆其肩」的造像特徵,我們因此知道,此二經所記的觀音,都是不空羂索觀音的形象。烏荼版《入法界品》的觀音形象,因此很明顯的是由南天金剛頂發展出來的不空羂索觀音的形象。武氏時代及其之前中國所譯的《華嚴經•入法界品》,都沒記載不空羂索的信仰及面貌,烏荼版《入法界品》出現這種變化,說明了烏荼版的《入法界品》的確是經過「金剛頂化」,並成為烏荼文化的產物。
烏荼版《入法界品》既能代表烏荼的佛教文化,因此有進獻中國的理由,特別是烏荼當時所發展的就是《入法界品》的佛王文化。
結論
自大乘佛教在第一世紀崛起之後,其便是多樣化地不斷向前發展。從密教金剛頂派在南天的發展情形來看,佛教在印度的發展,並沒有出現於一地的規律性發展現象,也沒有一成不變地在教內發展。金剛頂在印度南部的崛起,便說明了這些大乘的發展現象。
在過去,我們總認為,佛教自脫離印度教自成一學派之後,佛教的發展方向便與印度教不同。當然有些學者,如木村西崖,在研究大乘密教的發展之際,也注意到大乘在發展的過程中有再受到印度教化的現象,而這種印度教化的現象,甚至早在大乘崛起不久便已經開始。[163]六世紀之後南天金剛頂派從印度教天王傳統的信仰模式中成立不空羂索觀音佛王信仰的史實,因此不是大乘佛教在發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第一次印度教信仰佛教化的現象。在此之前,第四世紀之後中國帝王使用的佛教天王傳統,也是印度教天王傳統佛教化的一個現象。[164]從此六世紀及四世紀印度教天王傳統佛教化的現象來看,印度教及佛教混合出現的局面都與大乘密教意識形態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這是不是說,大乘密教意識形態的發展,在印度始終無法擺脫深根蒂固的印度教密教信仰的影響?
163. 木村西崖,《密教發達志》,第一冊。
164. 並見拙作,《東南亞的「天王傳統」與後趙時代的「天王傳統」》。筆者在此文中談到印度教天王傳統佛教化的現象。
| 頁198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謝得士在處理東南亞的佛教及印度教發展現象時,也注意到第八世紀中期之後東南亞佛教有金剛乘(Vajrayāna) 的發展特色及佛教和印度教混合發展的特色等。他認為,東南亞其時佛教出現這些特色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帕拉王朝(Pālā) 及那爛陀(Nālandā) 佛教信仰的影響。[165]謝得士似乎不知道,其所言的「金剛乘」,乃指本文所言的「金剛頂派」,是南天發展出來的密教信仰學派。八世紀的那爛陀及帕拉王朝,是中天胎藏派的發展地。南天及中天的密教發展,就八世紀的發展內容及情況而言,有一定的區別。木村西崖在其《密教發達志》中便一再的說明此一事實:「金剛頂自是成南天密教精髓者,而與胎藏法之成于中天,其根基全殊而不一焉。」[166]謝得士似乎也不知道,七、八世紀之後的東南亞,由于金剛頂的信仰是佛教發展的主流信仰,而金剛頂的信仰,從一開始便深受印度教的影響,因此東南亞在發展金剛頂信仰之際,便會出現印度教及佛教混合發展的特色。
約翰•密細也注意到東南亞有發展金剛頂密教的現象。他說,金剛智來華之前,他曾在717-718之間去了蘇門答臘(Sumatra)及爪哇,而其所譯的《大毘盧遮那經)》(the Mahavairocana)及《金剛頂瑜伽經》(the Vajrasekhara),在爪哇地區成為非常重要的典籍。[167]金剛智的爪哇及蘇門答臘之行及其所譯的金剛頂經在爪哇被重視的現象,事實上也能說明,760始造的婆羅婆多遺址為何會使用烏荼版的《入法界品》作為建造此遺址的造像內容之原因。
金剛頂的出現,再一次的讓筆者堅信,大乘佛教的發展,一直是與佛教意識形態的發展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金剛頂如果沒有成立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其是不可能成為南天幾百年的文化發展主流,也不可能將其成立及發展的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傳播到南海諸國及中國,并成為此些地區長時期的主流政治文化;更不可能在《華嚴經》文化的發展中造出烏荼版的《入法界品》。 種種的現象都說明,大乘佛教文化的發展,如果沒有政治的原因使然,其是不可能出現如此長久且多樣的面貌,也不能廣傳至如此多的地區。
金剛頂成立的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自第六世紀末出現之後,其傳播的地方實際上比本文所述的地點更為廣泛。中譯佛教文獻便記有,金剛頂的密教觀音佛王傳統也傳至中亞的于闐,并影響于闐成立自己的觀音佛王傳
165. G.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p. 96.
166. 木村西崖,《密教發達志》,上冊,頁343。
167. John Miksic, Borobudur-Golden Tales of the Buddhas, p. 21;也見《貞元錄•沙門跋日羅菩提傳》,卷十四,頁875-876。
| 頁199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統。
《觀自在菩薩阿麼■[齒*來]法》是一部沒有譯者或作者名字的金剛頂經典。由于此經出經的背景是在于闐,此經可能便是在于闐出經,或是記載于闐發展密教觀音佛王傳統的經典。我們知道此經是金剛頂經典的原因,乃是此經提到:「若欲持此真言求見觀自在菩薩者,結護加持供養儀軌,並依大教所蘇悉地經及金剛頂瑜伽所說次第……」等說明金剛頂信仰的語言。[168]此經的著作,基本上就是要說明,于闐有王施行密教觀音佛王傳統治世。此經一開始便說:
昔于闐國有清信士,精心持念觀自在菩薩真言,願見大聖,彌歷年歲不遂宿心。執志不易,倍復精勤。後于一夕,聞空中聲曰:汝往鄰國,謁彼某王。行者依言即往彼國。聞王法令非常嚴酷,有犯必刑。修行者遂謁其王,因蒙汲引詢問所欲。白以本求,遂近入後宮。悉如剎土,王乃 觀自在菩薩也。行者白菩薩曰:大聖治化豈用於刑戮乎?大悲何在?菩薩告曰:此土眾生,剛強難制,吾愍誘道,分身為王,所刑戮者皆化人耳。使彼獷俗畏威從風,政令若成,吾當隱矣。[169]
于闐地方的王現觀音相貌統治于闐地方的故事,看來具神話性,事實上,這個故事就是記述于闐有王施行密教觀音佛王傳統治國的事。如果不知道金剛頂有成立密教觀音佛王傳統的背景,也不知道密教觀音佛王傳統是實際的治國傳統,一定不會明白為何金剛頂會造出這樣的經典。雖然于闐觀音佛王傳統的發展與南天金剛頂的信仰有直接的關系,然就于闐觀音佛王手部的造像法:「前二手風頭箜篌,左一手掌摩竭魚,右一手持吉祥鳥白色,」[170]與不空羂索觀音的手部造像法有顯著不同此事,此于闐觀音佛王傳統,很可能就是于闐立於不空羂索觀音佛王傳統改造出的于闐觀音佛王傳統。無論其真實的情形如何,南天金剛頂法在亞洲的傳播,比我們知道的還要廣闊。
金剛頂所成立的密教觀音佛王文化,在七、八世紀之後,事實上已成為亞洲許多地區的主流文化。譬如,西藏自接受此佛王文化之後至今,達賴喇嘛尚施行無違。這就是今日達賴喇嘛尚有觀音化身之說,其所住的宮殿有觀
168. 觀自在菩薩阿麼■[齒*來]法,《大正》卷20,頁502下。
169. 同上,頁502中。
170. 同上,頁503上。
| 頁200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音宮殿布達拉宮(Potala)之名的原因。
在過去,我們都不知道,南天金剛頂的密教文化,原來是七世紀之後亞洲流行的主流文化,也不知道,中國在此文化的影響之下,金剛頂的佛王文化在武則天立國的初期(693)便進入唐庭,成為武氏一時使用的佛教治國意識形態。武氏之後,唐代帝王與此文化的接触,到唐德宗為止,至少有百年之久。這中間,此佛王文化,幾度都又成為唐代的國家信仰或國教。譬如,唐中宗(705-710)及唐代宗(764-780),[171]便都有明顯使用金剛頂佛王文化治國的現象。這也是我們在過去都不知道的事。中國只有使用儒家意識形態治國的說法及中國沒有使用佛教意識形態治國的說法,的確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171. 有關唐中宗施行佛王傳統治世的事,參見拙作,《龍門擂鼓台三洞的開鑿性質與定年》,龍門石窟研究所編,《龍門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頁166-182;有關代宗使用金剛頂佛王文化治國的事,將另文解說。
| 頁201 | 從南天烏荼王進獻的《華嚴經》說起- 南天及南海的《華嚴經》佛王傳統與密教觀音佛王傳統 |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第五期(2000.07) |
附錄:

柬埔寨吳哥八雍遺址的“普門世間主菩薩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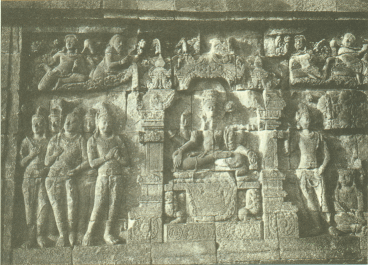
印尼爪哇婆羅多遺址的六臂不空羂索觀音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