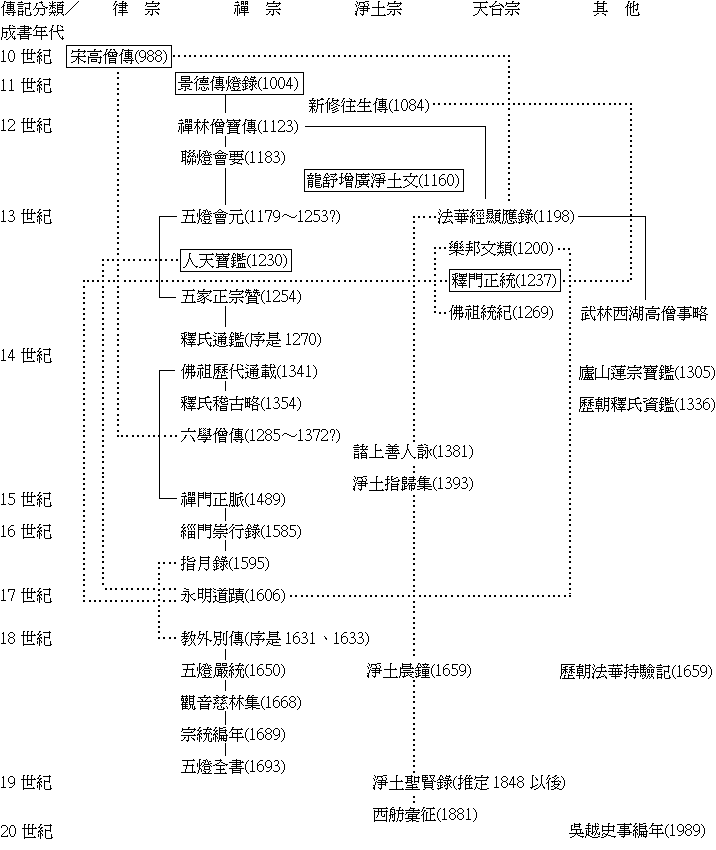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文學博士 釋智學
法光學壇
第五期(2001)
頁58-82
©2001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臺北市
| 頁58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提要:
生存在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國的永明延壽(904~975),向來以『萬善同歸集』的禪淨融合說知名,而且他的主著『宗鏡錄』是以禪、天台、華嚴、法相等四宗之說形成其心學。他的思想、主張,其實也已經反映出他所生存的時代的思潮、社會的環境,及佛教界的變化。所以筆者意圖藉由文獻學的方式,剝離後世傳記中非原有的描述,詳細檢證他的相關傳記,試圖還原其人的真實面貌。
文中所附的〔表一〕、〔表二〕,是筆者網羅各相關典籍,依年代先後(〔表一〕)及項目之別(〔表二〕),具體地比對‧配列各文獻的成果,希望藉此清楚地呈顯出受到時代思潮及宗派理念影響的永明延壽的面貌之變遷。換句話說,筆者意圖透過文獻學的方式,以歷史變化的角度表明,不僅每個個人都在寫歷史,其實時代和社會、歷史也透過當時當地特有的認知而正在塑造個人。
關鍵字:永明延壽、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
| 頁59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A Study on the Biography of Yung-ming Yen-shou
Shih, Jhi-xue
Yung-ming Yen-shou (904~975) who liv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countries in Wu-yüeh, has always been famous for the theory of harmonizing ch'an and pure land which he detailed in his Confluence of Everything Wholesome. In his main work, The Essential Mirror, he formulated his teaching of the mind based on four schools -Ch'an, T'ien-t'ai, Hua-yen, and Fa-hsiang. His concepts and ideas reflect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hanging Buddhist world of the times he was living in. An attempt is made here to reconstruct the true face of Yung-ming Yen-shou by removing via the philological method those parts of his biography which are later additions, and subjecting the relevant records to detailed scrutiny.
All relevant sources the present writer was able to locate have been arranged in synoptic manner according to date (Addentum I) and item (Addendum II).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rangement of material will help to demonstrate clearly how the picture of Yung-ming Yen-shou changed due to influences of intellectual fashion and sectarian viewpoints. In other words, the present writer is trying, by way of the philological method, to show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change not only that every person is writing history but also that the times, the society, and history model the shape of the individual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specific to that time and space.
| 頁60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一、關於現存資料
記載永明延壽傳記的文獻資料為數不少,〔表一〕裡所顯示的諸項文獻資料主要是從《大正藏》和《卍續藏》中檢索所得,其中,最古老的文獻是988年成書的贊寧《宋高僧傳》[1],而年代最新的文獻則是1989年編纂的諸葛計‧銀玉珍主編的《吳越史事編年》,至於可稱為最詳細的文獻則是大壑於1606年編著的《永明道蹟》。〔表一〕所顯示的各文獻的宗派分類,則是依照各文獻的作者的所屬宗派予以分類。易言之,這些傳記是由西元988年到1989年之間,基於各文獻的作者的所屬宗派、理念,被編纂而成的。至於各傳記相互間的關連,如果是屬於直接關係是以「──」表達,若是屬於間接關係則以「……」顯示。又若有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傳記文獻,例如包含有獨特資料的傳記文獻則以⃞表示,而且將在〔表二〕裡,比較各傳記的內容。
至今為止已發表的有關永明延壽傳記的論文,大部分是以《宋高僧傳》和《景德傳燈錄》等的記述作為中心而展開議論的,在諸篇論文中,列舉載述延壽傳記的資料最多並予以分類的是韓京洙氏的論文「永明延壽の禪淨融和思想」[2]。但是,韓氏所列舉的傳記雖最多也
1. 關於《宋高僧傳》,Heng-ching Shih作了如下的評述,“which(《宋高僧傳》)was only 14 years after Yung-ming's death, the account of Yung-ming's biography in it should be the most reliable.”(參照:The Syncretism of Ch'an and Pure Land Buddhism,頁94)
2. 參照:韓京洙[1988]「永明延壽の禪淨融和思想」(《印佛研》37~2,頁129)。在論文中,韓氏判斷云「記載延壽傳記的文獻,除了《宋高僧傳》以外,還有二十種左右。但是它們的內容幾乎都相同。而且可將它們分類為以禪為中心的傳記,及以淨土‧以天台為中心的傳記。」(由筆者中譯)對於這樣的分類,或者由於該書著者的立場無法明確地分類,或者由於該書著者並未擁有獨立的立場,當然確實有其實際上的困難。舉例來說,《廬山蓮宗寶鑑》是白蓮宗普度所編著的書籍,但是作者在製作〔表一〕時,將這本書列在「其他」欄裡。理由是因為,在中國佛教史上,白蓮宗向來不被視為正統派的一支,不太受承認。
在此順便一提有關白蓮宗的研究資料,提供參考。它們是,重松俊章[1933]「初期の白蓮教會について」(《市村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頁361~394),小川貫一[1944]「元代白蓮教的刻藏事蹟」(《支那佛教史學》7~1),小笠原宣秀[1963]《中國近世淨土教史の研究》(京都:百華苑),野口鐵郎[1986]《明代白蓮教史の研究》(東京:雄山閣)。
又,有關普度的研究資料,有小笠原宣秀[1950]「元代普度の白蓮宗復興運動」(《佛教史學》1~4,頁1~12),安藤智信[1980]「元の普度撰《上白蓮宗書》の歷史的意義」(《佛教の歷史と文化》,頁340~355)等等,值得參考。
| 頁61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僅達二十種類,而且他也僅將這些資料簡單地分類為禪、淨土、天台的三種;但是只要當我們參考下面所列的〔表一〕,就可以知道這種分類方式是相當不充分的。那麼筆者製作的〔表一〕之意義何在呢。概要而言,可以下列三點說明。即:
第一點是意圖藉以呈現出作者網羅收錄於《大正藏》和《卍續藏》等藏經中的永明延壽傳記的結果。
第二點是想呈現出,在各文獻當中透露出來的延壽傳記內容之間的相互關聯。
第三點是想呈現出,載錄永明延壽傳記的各文獻所蘊含的宗派性立場。
縱然如此,以第三點而言,也有如同大壑一般的人,因為他必須站在永明寺的後繼者的立場,也就是說,他必須採取禪宗的立場以編述永明延壽的傳記;然而儘管如此,他所編著的《永明道蹟》這本書卻是延壽傳記的集大成,這是因為其中甚至連其他宗派所傳承的延壽的事蹟也網羅在內的緣故。除此之外,由〔表一〕還可看到以下所列的其他現象。
首先是,禪宗的勢力隨著時代的進展,愈益強盛(確實,禪宗的勢力從六祖慧能以來已經在中國社會裡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天台宗自五代十國以來即迎向復興期,而且天台系淨土教[3]的發展也引人注目,這種台淨雙修的傾向和禪淨雙修的發展同樣都值得注意。
3. 中國天台宗裡,從智者大師以來,已經看得到對彌陀淨土的信仰。但是,古來被視為智者大師著作的《觀無量壽佛經疏》,一般說來,現在則是以偽作的見解比較有說服力(佐藤哲英《天台大師の研究》頁567~601)。進入宋代之後,天台宗第十四祖的四明知禮(960~1028)以及其同門師兄弟慈雲遵式(963~1032)一面興隆天台宗,一面也努力念佛並撰述著作。以這二位大師為首,神照本如(982~1050),神悟處謙(1011~75)孤山智圓(976~1022)等人也陸續地吸收淨土思想。特別是「唯心之淨土,本性之彌陀」(《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五,《大正藏》46,頁899中)的這種看法,是由知禮首先表現出來的。大致上從宋代以後,視彌陀淨土為唯心淨土的主張相繼地出現,這一主張遂成為中國淨土教中主要的淨土觀(參考:柴田泰[1989]「指方立相論と 唯心淨土論の典據」,藤田宏達博士還曆紀念論集《インド哲學と佛教》頁657)。關於天台宗淨土系的相關研究,有山口光円[1967]《天台淨土教史》(京都:法藏館),福島光哉[1995]《宋代天台淨土教の研究》(京都:文榮堂)等等。
| 頁62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至於律宗,令人感受到的是這一宗派的發展很微弱。最後應該提起的是淨土宗,這一宗的書籍有:王古(《新修往生傳》的作者)、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的作者)、彭希涑(《淨土聖賢錄》的作者)、周克復(《淨土晨鐘》的作者)等列位居士的著作,對於這件事我們不妨認為它呈現出宋代以後中國佛教中的「居士佛教」[4]的一個特色。
本文中另附〔表二〕。〔表二〕是參考〔表一〕的結果,並進一步由其中挑選出具代表意義的著作,意圖藉由所列各項目的對照,以顯示出永明延壽傳記在歷史發展上的全貌。〔表二〕裡所載錄的各傳記資料的記載,其中雖然有些資料彼此有相當大的歧異,即使如此,但是各傳記的資料並不是毫無根據地、隨個人所好地記載下來的,其中甚至也有明白顯示典據的傳記文獻,例如,宋‧志磐《佛祖統紀》中明言所載述的事跡「見本傳‧龍舒文‧臨安志」[5]、宋‧宗曉《法華經顯應錄》文中說「師(作者案:指延壽)事跡見大宋〔高〕僧傳‧僧寶傳‧寶珠集‧東坡大全」[6],元‧熙仲集《釋氏資鑑》中則記載資料來源是《編年》。又,和永明延壽有關連的作者也有幾位,例如,覺範慧洪(《禪林僧寶傳》的作者)、大川普濟(《五燈會元》
4. 關於居士佛教,可以參考:禿氏祐祥[1936]「居士佛教について」(《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1),小川貫一[1950]「居士佛教の近世的發展」(《龍谷大學論集》339號),同氏[1951]「居士佛教の倫理的性格」(《龍谷史壇》35號),以及同氏[1962]「中國における居士佛教と倫理」(《日本佛教學會年報》27號),加地哲定[1975]「中國居士と佛教」(《密教學會報》14號)等論文。
5. 志磐《佛祖統紀》卷26(《大正藏》49,頁265上)。又《佛祖統紀》的永明延壽傳文中引用了慧洪《禪林僧寶傳》的內容,這件事可以從他引用了「惜吾不及見耳」這句話而得知(《大正藏》49,頁264下)。
6. 《卍續藏》134,頁865下。又,關於《寶珠集》的著者,有王古及陸師壽的兩種見解,其後根據岩井大慧氏等人的研究,確定了著者是陸師壽。現今這本書被視為八卷本,收錄於《續淨土宗全書》第十六卷。相關的研究論文有,岩井大慧[1957]「淨土寶珠集の撰者について」(《日支佛教史論考》頁319~355,東洋文庫),深貝慈孝[1975]「往生傳、高僧傳解說──特に淨全續十六卷所收本について──」(《淨土宗典籍研究》頁808~829,東京:山喜房),高雄義堅[1975]《宋代佛教史の研究》頁116,等等。
取材自《東坡大全》的引用是,蘇軾記載永明延壽放生的文章(參考:《東坡志林‧仇池筆記》頁66~67,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一版)。
| 頁63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的作者)以及石芝宗曉(《法華經顯應錄》的作者)、曇噩(《六學僧傳》的作者)、大壑元津(《永明道蹟》的作者)等人都和永明寺(後名為淨慈寺)有關係。還有曇噩也和延壽曾經住錫過的靈隱寺有關係[7]。雖然如此,但是若將〔表一〕的資料全部都載錄到〔表二〕裡,則內容將變得很厖雜,所以筆者由這些資料中,選錄出撰作年代最接近延壽的生存年代的贊寧《宋高僧傳》卷28,和道原《景德傳燈錄》卷26、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卷5等三本典籍,以之為基本資料。而這三本著作按照順序來說,各自是代表律宗、禪宗以及淨土宗的立場。
上述的三本著作中,《宋高僧傳》一書在贊寧編纂時,曾費了相當大的苦心。《宋高僧傳》的特色在於重視且豐富地運用碑銘、塔銘類的資料(一手資料)[8],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其缺點,這就是當贊寧採用這些碑銘、塔銘類的一手資料時,他對於各史料可信度的檢討做得並不充分[9]。因此,筆者認為當我們在檢討延壽的傳記文獻時,《宋高僧傳》以外的資料也應該參考。
其次想談的是《景德傳燈錄》。關於這本書,柳田聖山氏在《祖
7. 「酉菴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元叟端補靈隱,門風高,非宿學莫敢窺其門。師直往咨叩,了無畏懼。機契,命掌內記。出世天台之國清。洪武三年(1380)詔徵江南有道僧,師居其首。」(《靈隱寺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第23冊,頁198)。
8. 參考:陳援庵[1962]《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頁39~41,北平:中華書局。
9. 參考:塚本善隆‧牧田諦亮《國譯一切經‧史部22》的《宋高僧傳》解題(東京:大東出版社,1978年改訂版,頁1~4)。又,阿部肇一氏在他的論文「《宋高僧傳》と《禪林僧寶傳》」裡,引用了上述牧田諦亮氏的意見,作出如下的敘述。「在法脈上屬於南山律系統的贊寧,他對禪家的有意乃至無意的疏忽,以及主要是身處江南的贊寧,他在資料的蒐集上可看得出是有偏見的。」緊接著,阿部氏又說,「可以看得出來在這兩者(筆者案:指贊寧《宋高僧傳》和慧洪覺範《禪林僧寶傳》)之間,有一些宗派意識上的對立。」(阿部肇一[1986]《中國禪宗史の研究》頁468,東京:研文,原為日文,由筆者中譯)。誠如上述,橫跨在各典籍之間的宗派意識的影響是不能忽略的。
順帶一提,〔表二〕裡之所以沒有載錄《禪林僧寶傳》,是因為該書中有關延壽傳記的記載和《景德傳燈錄》的內容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之故。至於其中寥寥可數的差異則載錄於「備考」欄。
| 頁64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堂集索引》裡這樣地描述它。
「《(景德)傳燈錄》預期法眼宗勢力的強盛,它是綜括唐代禪宗的典籍,……《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呈上朝廷,可以說是在北宋初期佛教界勢力重編的新氣氛當中,特別值得注目的事。可以說,《景德傳燈錄》是補《大宋高僧傳》缺陷的新型佛教史書」[10]。(原係日文,由筆者中譯)
此外,陳援庵在他的名著《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4裡,引用了晁公武《郡齋讀書誌》,而作出以下評語。他說:
「一部《景德傳燈錄》,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傳,惜乎歐(筆者按:指歐陽修)、宋(筆者按:指宋祁)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書》及《(筆者按:即新)五代史》皆闕失此等絕好資料。」[11]
關於這部《景德傳燈錄》的存在價值,雖然還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然而上面所引用的兩位先生的意見值得參考。而且《景德傳燈錄》中所記載的延壽傳記,和《宋高僧傳》的記載有不同之處,因此作者認為在〔表二〕裡載錄《景德傳燈錄》的資料,並加以比較對照,是不可缺少的作業。
接著筆者將說明為何選擇王日休所撰《龍舒增廣淨土文》的二大理由。理由之一是,王日休既承認心外有西方淨土的存在,又確信可以藉由念佛修持的善報而往生淨土。王氏本身同時也是著名的往生淨土的士大夫。理由之二是,王日休和一般所謂南宋初期佛教界的諸宗融和、禪淨雙修的風潮相互呼應,編纂《龍舒增廣淨土文》,廣泛地勸人修西方淨業,直到現今,這本《龍舒增廣淨土文》依然為修淨業人士所愛讀。除此之外,王日休也校訂出版了《大阿彌陀經》的四譯對照本[12]。如上所述,王日休其人及其著作都具代表性,而且對後世
10. 參考:柳田聖山[1984]《祖堂集索引》下冊,頁1589,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1. 參考:陳援庵[1962]《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頁92,北平:中華書局。
12. 參考:林田康順[1993]「王日休《龍舒淨土文》の研究(3)」(《大正大學大學院研究論集》17號,頁111~125),以及小笠原宣秀[1964]「宋代の居士王日休と淨土教」(《結城教授頌壽紀念‧佛教思想史論集》頁517~532,東京:大藏出版社)。
| 頁65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的影響也不小,因而筆者將《龍舒增廣淨土文》的內容載列在〔表二〕上。
還有,我們也應該注意曇秀的《人天寶鑑》。這部書自古以來就被當作禪宗七部書之一,一向受到喜愛和尊重。它也傳往日本,雖然傳入的時期並不清楚,但是在日本的南北朝時期前後已經印刷刊行了。現在,它作為五山版當中的一部書,收藏在大東急文庫裡。這部書裡所見到的延壽的傳記有其特殊之處,因此筆者認為有將它列入〔表二〕而予檢討的必要。順帶一提,關於這部書的作者曇秀其人,在《佛書解說大辭典》第八卷(頁383)以及篠原壽雄注解的《人天寶鑑》中,都將他誤認為是「黃龍慧南的法嗣」[13]。但是,生存在十一世紀的黃龍派開祖黃龍慧南(1002~1069)和在十三世紀(1230)時為《人天寶鑑》書寫自序的曇秀之間如何得以擁有師徒關係呢。總而言之,我們姑且將作者的問題擺在一邊,由於這部書能善巧地開啟人天的眼目,提供學習佛法的道路,自古以來就是廣受尊重的典籍。
最後想說明的是良渚宗鑑的《釋門正統》。這部書,一方面它是為了顯示天台宗的正統地位而撰述的,也就是說它是基於對抗《景德傳燈錄》等一連串禪宗燈史的意識而撰述的,而在另一方面,它被視為現存最古老的紀傳體佛教史,因此受到重視[14]。所以筆者認為將這本《釋門正統》和《景德傳燈錄》對照讀解的話,必然很有意義。
除了上述的五本文獻之外,也有值得重視的典籍,例如屬天台宗法脈的宗曉的《法華經顯應錄》以及同屬天台宗法脈的志磐的《佛祖統紀》[15]。至於其他的各典籍則幾乎僅只是根據這些重要典籍加予增
13. 篠原壽雄[1977]《人天寶鑑》頁7,東京:明德出版社。
14. 參考:牧田諦亮[1954]「宋代における佛教史學の研究」(《印佛研》3~2),以及高雄義堅[1975]頁141~142,陳士強「南宋元明清佛教史撰作評述」,(《復旦學報》1987年3期,頁64)。又,小川貫一氏在「宗鑑《釋門正統》の成立」的論文中也說,「良渚宗鑑《釋門正統》一書……作為志磐《佛祖統紀》的源流,有其重要意義。」(《龍谷史壇》43,頁15~21,1958年,原係日文,筆者中譯)。
15. 筆者未選用志磐所撰的中國佛教史籍名著《佛祖統紀》的理由有下列二項。
第一是,根據志磐的自序,《佛祖統紀》的編述是繼承景遷《宗源錄》、宗鑑《釋門正統》而得以完成的。而《釋門正統》一書既然已經載錄在〔表二〕上,所以沒有重複選用的必要。
第二是,《佛祖統紀》中有關永明延壽的記事有錯誤的情況。舉例來說,一方面該書卷43裡敘述了「〔開寶〕7年(974)二月,永明壽禪師示寂」,另一方面該書卷26裡卻又有不同的記載,即「開寶八年(975)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加趺而化」。既有這種錯誤,難免予人注意不足的印象。所以作者決定將《佛祖統紀》中應該注意的有關永明延壽的記述載錄於「備考」欄。
| 頁66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補修飾或予摘要所成。除了上述的典籍之外,其他性質的資料,比如說,地方志及佛寺史志中所收錄的資料也有值得參考之處。若具體說明書名的話,例如,潛說友《咸淳臨安志》等和《中國佛寺史志彙刊》所收錄的《淨慈寺志》、《雪竇寺志》等;但是這類資料都屬於後世的資料,而且其中也還殘留有部分疑問和未解決的問題,因此作者決定在考證永明延壽的傳記資料和檢討各資料中的問題點的時候,不將它們列入〔表一〕,而僅列入〔表二〕的「備考」欄,以供參考。若將各典籍中所載錄的永明延壽傳記一-介紹的話,文章將變得冗長,因此,在下文中,筆者將以敘述具根源資料性質的贊寧《宋高僧傳》卷28的記載為主軸而檢討〔表二〕的內容。此外,如果所記載的是《宋高僧傳》中所無,但卻是見載於其他文獻的有價值的內容,也將一併敘述。至於考證的部分,為了不影響行文,原則上放在注裡處理。希望透過這一處理過程,能清楚地呈現出記載永明延壽傳記的資料演變的情況。
二、永明延壽傳記的演變
──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16]──
釋延壽,俗姓王,本籍錢塘[17]。其實嚴格說來,《宋高僧傳》記載的「本錢塘人也」之說有必要作考證。這意謂著,根據《宋高僧傳》的這一說法,我們可以認為延壽祖籍錢塘,後來才遷往其他地方居住。關於這件事,我們也可以從宗曉《樂邦文類》、曇秀《人天寶鑑》等典籍中將他視為丹陽人而覺察。雖然筆者如此大膽推論,但在
16. 有關此一部分,筆者已以日文發表部分內容(請參考)《インド哲學佛教學研究》4,1996年12月)。
17. 參考〔表二〕的「名字與出身」欄。其中,道原《景德傳燈錄》認為永明延壽的出身地是餘杭,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則認為是丹陽,而曇秀《人天寶鑑》則彷彿是在調和上述二說似的,記載成「(祖)先(是)丹陽人,父移居錢塘」。
就錢塘的地理位置而言,根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0(頁3756,出版時地人不詳。東京大學漢籍コ~ナ收藏本)之說,它位於現在的浙江省杭州。而餘杭的話,依劉鈞仁[1980]《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第五卷中說,「隋屬揚州餘杭郡,唐屬江南道杭州,五代因之,宋代屬兩浙路臨安府」(頁2147下,東京:凌雲書房)。另外,《上海歷史文化名城詞典》則認為,錢塘及餘杭都位於現在的浙江省杭州(頁344)。
至於丹陽,劉鈞仁《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第一卷中說,「在江蘇丹徒縣東南七十里……唐改丹陽,屬江南道潤州。五代因之。」(頁62)。
| 頁67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目前的階段,也就是在尚未發現其他足以支持作者這一推論的典據時,暫時仍必須沿用距離延壽的生存年代(904~975)最接近的《宋高僧傳》(988年)及《景德傳燈錄》(1004年)兩部書的記載。
在吳越國統治兩浙地方的時代,延壽擔任地方公務員,負責軍隊的補給[18]。延壽的性格純正而且正直,不曾撒謊。當他誦讀《法華經》
18. 參考〔表二〕的「履歷」欄。《景德傳燈錄》文中說「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華亭」的地理位置,若依劉鈞仁《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第四卷之說,它相當於現在江蘇省松江縣(頁1674下~5上)。又,木田知生[1991]在「江浙初期佛寺考──佛教初傳南方ルート研究序說」的論文中說,「華亭縣(今上海市)」,但是木田氏完全沒有說明所依典據(《龍谷大學論集》439,頁59)。譚其驤[1982]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中,認為是在上海和嘉興附近的松江(頁89~90,上海:地圖出版社)。台北,三通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則認為是現在江蘇省松江縣西平原村(頁31,1984年)。又,在譚氏的地圖集中,紀元934年的地圖上還看不到華亭這一個地名,它的出現得等到紀元954年的地圖。然而,根據清‧孫星衍等人編纂的《松江府志》卷1「古今建置沿革表」來看的話,我們可知,由唐僖宗乾寧四年(897)開始,吳越國就一直支配華亭附近的地方,到後唐同光二年(294)時設立了華亭縣,其到後晉天福三年(938)時,華亭縣等地就被納入秀州的管理之下(《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10》,台北:成文)。照這樣看來,譚氏地圖集的記載應該可以說是不完整。如果我們將上述的諸多事實和永明延壽的生年(904年)對照來看時,則我們可以明白上述《景德傳燈錄》的說法相當值得參考。
順帶一提,關於當時華亭的佛教狀況,宋代楊潛《雲間志》卷中裡說,「浙右喜奉佛,而華亭為甚,一邑之間為佛祠凡四六」(『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北京:中華,1990)。
其次,我們來看看「鎮將」。關於這一官職及其職權,日野開三郎[1938]在「五代鎮將考」一文中認為,五代時期的鎮將所保有的職權,除了兵權以外主要有下列三種,也就是捕盜警察權,獄訟權以稅役徵科權(《東洋學報》25~2,頁224~27)。周藤吉之[1962]在「五代節度使の支配體制」一文中則認為「鎮將在掌理捕賊、獄訟、軍事時,也徵收賦稅,而形成了他在地方上的地盤。」(《宋代經濟史研究》頁635~636,東京大學出版會。原係日文,由筆者中譯)。上述兩位學者的檢討對象主要是以五代的情況為主,而對於僅屬於地方政權層級的十國的情況並未涉及。然而,由於唐代官制中也設有鎮將一職(參考:黃本驥《歷代職官表》卷6),再加上吳越國從開國君主武肅王錢鏐時代以後即奉領有中原地方的五代的正朔,當我們將這兩件事一起考慮時,筆者認為在吳越國內設立鎮將這一官職的可能性相當大。
再度將話題轉回永明延壽的傳記。關於出家以前的延壽所擔任過的官職的問題,當我們對比各資料時,可以發現各傳記所記載的官名雖然不同,但是幾乎所列舉的都是和稅金或和管理倉庫有關的官職,所以 Heng-ching
Shih 在其著作中,認為“Yung-ming served
as a tax offical”(參照:The Syncretism
of Ch'an and Pure Land Buddhism. p.92)。
| 頁68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時,誦經之聲不曾中斷過。當時,正值翠巖令參[19]致力弘法,延壽毅然捨離妻子兒女,剃除鬚髮,身著壞色衣,受具足戒,出家修行。
19. 參照〔表二〕的「出家師父」欄。有關翠巖令參個人的傳記,請參照《翠山寺志》頁69~71,此處省略不載,主要僅就延壽的出家年齡以及出家場所略作考察。
首先關於龍冊寺,根據《冊府元龜》卷52以及牧田諦亮《五代宗教史研究》(頁71)所載,清泰二年(935)文穆王錢元瓘曾向後晉請求勅贈「龍冊」的寺額,但受到拒絕,反而被命以「千春寺」之名取代。此外,在《宋高僧傳》卷13「龍冊寺道怤傳」中有關於龍冊寺的記載,即
「文穆王創龍冊寺,請道怤居之。以天福丁酉歲(937)八月示滅」(《大正藏》50,頁787上29~中1)。
又,《景德傳燈錄》中也有二則有關龍冊寺的記載,即,
「屬翠巖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延壽)禮翠巖為師。」(《大正藏》51,頁421下11~14。)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峰受記,止於翠巖,大張法席,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大正藏》51,頁352下~353上。)
當我們將以上各記載合併起來考慮時,翠巖令參住持龍冊寺的時期非在紀元937年以後不可。而延壽的生卒年又是在紀元904年到975之間,如此一來,《人天寶鑑》中所記述的延壽在34歲時(紀元937)出家的事情就變得很有可能,相反地,大壑《永明道蹟》所持的延壽於30歲(紀元933)出家之說則變得很不可能。此外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也就是,令參的徒弟子興明悟,他曾經繼令參之後住持龍冊寺(《景德傳燈錄》卷22,《大正藏》51,頁380下)。這件事應該可以視為令參曾經住持龍冊寺的傍證。
此外,關於延壽剃度的場所,有此一說。即,
「桃源之慈雲(寺),……五代德韶中興為第二道場。禪師(筆者按:指延壽)剃髮之所。」(《大明高僧傳》卷4「真清傳」《大正藏》50,頁914中10~14)。
這一說法雖然也見載於《天台山方外志》卷4(頁160)以及關口真大《禪宗思想史》(頁396)兩書,但其典據除了此處所列的《大明高僧傳》的記載之外,管見所及,遍尋不著。因此筆者認為此說僅是後世相傳之說,不足為據。
另外,當我們將《人天寶鑑》所持的三十四歲出家說和《宋高僧傳》所主張的「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大正藏》50,頁887中15)的兩種說法合併考慮的話,就變成延壽(904~975)是在三十四歲(937年)那年出家,於七十二歲(975年)時示寂。因此,這兩本書的主張各自都有成立的可能性,但是在這兩種說法之間卻有二年的差距。針對這一點可疑處,畑中淨園在「吳越の佛教」一文中曾予解釋,即「宋高僧傳所說的法臘三十七,其中的七字應可以認為是九字的印刷錯誤。」(《大谷大學研究年報》7,頁326,1977年。原係日文,由筆者中譯)。畑中氏的這一主張相當有說服力。相反地,屬禪宗系統的《景德傳燈錄》以及慧洪《禪林僧寶傳》等書所謂的「春秋七十二,法臘四十二」之說法,應該可以說是錯誤的。
| 頁69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據說延壽曾在天台山的天柱峰修行為期九十日的禪定[20],當他作定期間,據說有一種名叫尺鷃的小鳥曾經在他的衣裡作巢。(因為他這般地努力於禪定)終於獲得天台德韶的印可,證明他修行有成。後來延壽曾經移往雪竇山[21]。他在弘法之餘,多是在瀑布之前坐禪讀經。三衣中並無以繒纊製作者,而是以布襦度日。他的飲食簡單,僅配一
20. 在《景德傳燈錄》記載為「天台山天柱峰」(《大正藏》47,頁148)。其他的資料也幾乎相同,只有宗曉《樂邦文類》(《卍續藏》107,頁910下),以及《天台山志》卷八(《天台山方外志》頁352)二書當中記載為「天台山智者巖」。
又,關於天台山,延壽自己也曾經以位於此山的國清寺作為比喻,他在《宗鏡錄》卷18文中,藉之說明「不共作一佛,不各各自成」(《大正藏》48,頁514下15~19)的意義。
關於九十日習定,我們由《文殊問般若經》和智顗《摩訶止觀》第二上的四種三昧的見解來看,可以知道這種禪定法門應該和一行三昧有關係,所以宗曉在《法華經顯應錄》中說延壽「於國清行法華三昧」。對於宗曉的這一說法,我們宜略作考證。延壽他在《宗鏡錄》中曾經提起「國清寺」一次(《大正藏》48,頁514下15),提起「法華三昧」二次(《大正藏》48,卷27頁569中15~28,卷35頁619下1),提起「一行三昧」二次(《大正藏》48,卷34頁615下8,卷81頁862中~下)。對於這二種修行法門和永明延壽的關係,其實有必要作詳細分析,特別是「法華三昧」和延壽的淨土法門或許頗有關聯。筆者之所以如此推測,是因陳敏齡氏在「天台淨土教的往生表現」一文中,曾經提起從以前開始,在一般的思潮當中,就有一種是將修行法華三昧視為是往生阿彌陀淨土的原因。不過筆者的這一推測有待將來的詳細研究。
此外還有一件事,即在《文殊師利問經》文中說到「復於九十日修無我想,端坐念佛,不雜思惟。除食及經行、大小便時,悉不得起。」(《大正藏》14,頁507上),而《宋高僧傳》中的延壽傳也說「有鳥類尺鷃,……巢棲於衣裓中」,我們將這兩段文字敘述合併起來考量時,延壽在天台山天柱峰修行一行三昧法門的可能性就變得非常高。也就因此,明‧幽溪傳燈就曾經說過「壽公(筆者案:指延壽)入定於天柱」(《天台山方外志》頁50,《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3輯第8冊)。
其他需須注意的相關問題是禪宗和一行三昧的關係,關於這一問題,請參考柳田聖山著,吳汝鈞譯《中國禪思想史》(台北:商務,1985年三版,頁71~85)。
最後,關於「法華懺」,它也是相關的問題,必須一併考慮。請參考〔表二〕「懺悔」欄,以及註[32]。
21. 請〔表二〕的「住雪竇」欄。有關雪竇山(後世稱為資聖),在常盤大定等編纂《中國文化史蹟》解說篇上冊第四卷裡提及它「位在浙江奉化縣西北五十華里左右的雪竇山巔。雪竇山屬於四明山。……它是天下禪宗十剎之一。……五代時期的廣順二年(紀年952年。但是在《雪竇寺志略》頁13中記載為「廣順三季」),法眼三世的智覺延壽曾經將之改建一新,宋代淳化、咸平年間(990~1003),獲賜資聖寺寺額……。」(頁134)。而在《雪竇寺志略》一書中說,「(雪竇)寺,……後湖海稱〈二覺道場〉,以智覺(筆者案:指延壽)、明覺(筆者案:指雪竇重顯)為重。」(參照:《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3輯第13冊,頁76)。還有在山夫行編、道嚴行補的《雪竇寺志》(1681年刊)一書中說,「至吳越錢氏,命壽公智覺禪師住持」(參考:《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3輯第13冊,頁66)。此外,在《淨慈寺志》卷首一裡也敘述了「天台韶國師深器之,為付囑。出住雪竇山」一事(參照:《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17冊,頁62)。如上所述,以《宋高僧傳》為首,幾乎所有的傳記資料都記載了延壽曾經住錫雪竇的事實。根據上述諸典據,筆者認為延壽和雪竇山的關係可以確認無誤。而且根據《淨慈寺志》之說,我們可以進而了解延壽住錫雪竇,是基於他和天台德韶的師徒關係。
| 頁70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道菜餚,而且吃的是野菜,並採斷中齋的方式[22]。漢南國王錢氏相當敬重他,曾經請他施行方等懺[23]。此外,他也購買小動物放生[24]。延
22. 關於「斷中」這一詞彙的意義,學術界研究至今,作出了下述幾項解釋。
(1)小野勝年氏在「斷中の語義について」文章中說,「所謂斷中,也可以代換稱為終中或盡中,……也常常被當作〈斷中齋〉的省略語。」然後又說「〈斷中〉意指一天當中的最後一餐」(《東洋史研究》17-4,1959年,頁93~98)。
(2)牛場真玄氏在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に見える「斷中」についての再考」一文中,提示出四點結論。筆者認為當中特別重要的一個段落如下。即,「第二點,從時間上來看,午齋時間是在正午時分,相對於此,〈斷中〉則應是指中午之前的飯食。……第四點,斷中是和五台山的文殊信仰相結合的活動。」(《東方學》31,1962年,頁77~92)。
(3)上村真肇氏則認為〈斷中〉是吃中飯的意思(《慈覺大師研究》頁586,頁604,1964年)。
(4)福井康順氏[1990]卻說,所謂斷中和中斷的意義相同(《日本天台の諸研究》頁379)。
(5)足立喜六譯注,鹽入良道補注《(圓仁)大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中,主張:有在午飯前或午飯後長時間休憩二、三小時,或睡午覺的習慣,這就稱為斷中。(頁245~246,東洋文庫157,1970年初版一刷,1994年初版18刷)。
此外,《宋高僧傳》文中的「斷中」一詞的用例,除了卷28「延壽傳」之外,還出現在卷21「寧師傳」。相關用語的「時中」也可見到一個用例。首先,卷21「寧師傳」中所見「斷中」的用例,其內容是「寧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大正藏》50,頁849中12~14)。而「時中」的用例則出現在卷24「智燈傳」,其內容為「釋智燈,不知何許人也,矜莊己行,嚴厲時中」(《大正藏》50,頁866下6~7)。當我們將以上三個用例一起考量,而檢討《宋高僧傳》「延壽傳」中「野蔬斷中」的文意時,牛場真玄氏所主張的「斷中是和五台山的文殊信仰相結合的活動」之見解,其實並不適用於解釋「延壽傳」文中的「斷中」。所以筆者認為針對《宋高僧傳》文中所出現「斷中」的語義而言,應以小野勝年氏的意見較為妥當。
23. 關於方等懺法,小林正美氏在「智顗の懺法の思想」一文中說,「所謂方等懺法,是根源於北涼‧法眾譯《大方等陀羅尼經》的懺法,它與智顗所思考創設的法華懺法不同,是早在智顗以前就相當廣泛流行的懺法。」(參照:小林正美「智顗の懺法の思想」,《六朝佛教思想の研究》頁358,東京:創文社,1993年)。對於方等懺法和法華懺法這二種懺法,小林正美氏認為「這兩種懺法由全體構造來看的話,幾乎可以等同視之。」(參照:同上,頁360)。
其次,我們由延壽的諸著作,如《宗鏡錄》和《智覺禪師自行錄》、《萬善同歸集》等書中搜尋「方等懺法」一詞的用例時,僅只發現二個,而且這兩個用例都源自同一件事情。也就是在《萬善同歸集》卷上所記載的有關智顗的師父慧思修行方等懺的記事(《大正藏》48,頁965下16,頁965下29~966上1)。其實,誠如《宋高僧傳》中「延壽傳」與注(20)中所見,延壽曾經在那座與智顗關係深切的天台山修行,所以假如延壽修行方等懺的話,我們應可以推定他的修行方式必然是與天台宗的方等懺法淵源頗深。因此,筆者認為在解釋《宋高僧傳》「延壽傳」中「方等懺」的意義時,小林正美氏的意見相當值得參考。此外,請參考〔表二〕的「懺悔」欄。
24. 關於延壽實行放生活動一事,這在《宋高僧傳》以後的載錄延壽傳記的相關各典籍裡幾乎都很明確地記載了。特別是《東坡志林》的「延壽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為放生之用」之記載特別受注目(蘇軾《東坡志林‧仇池筆記》,頁66,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一版)。以後,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與宗曉《法華經顯應錄》等書也繼承上述《東坡志林》的記述,至大壑《永明道蹟》時,延壽放生之說發展成老人率領數萬隻魚蝦前來向吳越國王說明延壽的善行,並向吳越國王乞求原諒延壽「盜官錢」的行為(《卍續藏》146,頁978下)。良渚宗鑑《釋門正統》中言及「〔延壽〕乞西湖為放生池」(《卍續藏》130,頁899上)。王在晉「放生池記」文中則敘述「〔西〕湖南淨慈寺山門臨水,為永明壽禪師放生處」(《淨慈寺志》3,頁931)。
然而在延壽自己的著作中,提及「放生」的僅可見於二個地方,即《智覺禪師自行錄》的一處(《卍續藏》111,頁165上)以及《萬善同歸集》卷中的一處(《大正藏》48,頁981下19~982上1),至於百卷的《宗鏡錄》卻全無隻字片語言及。因此,放生這件事在延壽個人的修行觀上占有怎樣的地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順帶一提,畑中淨園氏在其「吳越の佛教」一文中主張,延壽之所以獲得免除死罪之原因,乃在於吳越文穆王為了替其父武肅王錢鏐超薦追福,以延壽將來必須出家作為條件,免他一死,而將他放逐到翠巖寺,四年之後,延壽隨侍其師翠巖令參遷住龍冊寺。但是,畑中氏雖然如此主張,卻沒有典據的支持,再加上這一主張的本身也忽略了延壽本人的出家熱誠。所以筆者認為畑中氏的意見不過只是他個人推測的結果罷了。
| 頁71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壽廣泛地愛護生物,待人接物慈悲柔和;縱使受到不合理的待遇,也不會因此發怒而形諸神色。延壽在一生裡所讀誦的《法華經》累計共達一萬三千餘部[25]。延壽更是經常勸信徒們恭造佛塔和佛像[26]。他雅
25. 筆者認為延壽之所以熱心誦持《法華經》和淨土法門不無關聯。在現代學者當中,雖然有人認為致力於萬善行道的延壽所依據的淨土經典具體而言其實並不明確(柴田泰[1965]「宋代淨土教の一斷面」,《印佛研》13-2,頁236下),但是筆者卻認為延壽的淨土法門是和他讀誦《法華經》有所關聯,理由如下。首先,我們先注意《法華經》所流行的地域範圍,就這一點而言,佐藤心岳氏指出,《法華經》的研究、講說在隋唐時代,是在以長安、蘇州、浙江省的餘姚、浙江省的天台山等地為中心的地域,而且在這些地域,《法華經》的影響也極為明顯(「隋唐時代における《法華經》の研究講說」、《惠谷先生紀念論文集‧淨土の思想と文化》頁1156,京都:佛教大學,1972年)。而且延壽的祖國──承唐代餘緒的五代十國中的吳越國,其勢力範圍包含了餘姚、天台山,因此延壽之讀誦《法華經》,也可以視為接受地域文化傳統強烈影響的結果。再說,延壽個人也曾在天台山修行,和天台山的因緣匪淺。
其次,當我們從延壽的修行層面來看待,在記載他修行法門最詳細的《智覺禪師自行錄》中,他每日所力行的百八件佛事之中,和《法華經》有關聯的是,第1件的「法華堂」、第2件的「法華懺」、第6件的《法華經》、第15件的「同證法華三昧,咸生彌陀淨土」、第41件的「頂戴法華經行道」及第78、84、99件佛事等。延壽之所以終其一生讀誦《法華經》並將之付諸實踐,想必是受到如果受持、讀誦、書寫《法華經》,則可以獲得莫大的功德的思想風潮不無關係(道端良秀「中國佛教と《法華經》の信仰」、《中國佛教と社會との交涉》頁94,京都:平樂寺書店,1980年)。此外,阿彌陀佛信仰也對《法華經》的內容有所影響,這一點是石上善應氏所提起的(「淨土思想と法華經の交涉」,塚本啟祥編[1982]《法華經の文化と基盤》頁468,京都:平樂寺書店,1982年)。但是應該注意的是,石上氏之說主要是根據他研究梵文本《法華經》所得知的結果,其中他並未言及漢譯本法華經和淨土思想的交涉,所以應該還有作進一步論議的餘地。
最後想討論的是,中國的禪師和《法華經》之間的關係。其一是《法華經》經常被活用為禪機。其二是,後世為《法華經》作注釋的禪師為數不少(櫻井秀雄[1982]「中國佛教における禪と法華經の交涉」,塚本啟祥編《法華經の文化と基盤》,京都:平樂寺書店,1982年)。由此來看,延壽重視而且實踐《法華經》一事,並非不可思議之事。不過話又說回來,這是後世的發展傾向,它和五代宋初的延壽之間有多少關聯,仍有待檢證。
附帶一言,延壽讀誦《法華經》一事,不僅流傳在他的相關傳記資料裡,到後世,甚至也孕育出雨華臺(又名法華臺)的傳說。例如,《湖山便覽》中記載,「雨華臺,一名法華臺,在萬峰房西。《淨慈寺(舊)志》謂延壽就此課《法華經》,嘗感四天花雨。」(《淨慈寺志》卷4,頁320~1)。又,《釋門正統》的延壽傳文中有「誦蓮經」之一語。所謂「蓮經」,這在《宋高僧傳》文中也可見,即指《法華經》(參照:卷25「守素傳」、《大正藏》50,頁868上28~中4)。此外,也有「法華堂」的記載流傳著(《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111,頁154下5)。正因為有上述的諸般傳承,所以大壑才會在《永明道蹟》文中記載延壽「一生隨處常建法華堂」、「於慧日峰誦《法華經》,感諸天雨華,成雨華臺。」(《卍續藏》146,頁980上1)。
26. 關於延壽造佛像及佛塔之事,在傳記資料中,除了《宋高僧傳》提起之外,僅有良渚宗鑑《釋門正統》(《卍續藏》130,頁899上3)和《新修科分六學僧傳》(《卍續藏》133,頁583上)兩部書言及。延壽所著的《萬善同歸集》卷中也提及造佛像及佛塔(《大正藏》48,頁979下~980中),但是在詳載延壽日常修行的《智覺禪師自行錄》中卻完全沒有觸及。請參考〔表二〕的「造塔像」欄。
然而,如果依據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和《淨慈寺志》、《武林梵志》、《大明一統志》等書,我們可以知道延壽曾建立六和塔。例如,《武林梵志》記載「六和塔,在月輪峰傍,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建。……智覺禪師乃即錢氏南果園建塔,以鎮江潮。高九級,五十餘丈」(《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7冊,頁154)。又在《靈隱寺志》卷6「治潮皆靈隱僧論」(同上,第1輯第23冊)及《十國春秋》卷89「僧贊寧傳」中都記載,贊寧和延壽禪師一起建塔及寺以鎮錢塘潮。這也就是說,六和塔的完工是延壽和贊寧兩人努力的成果。因此,六和塔和延壽有所關聯,勿庸置疑。日本學者石井修道氏說「六和塔,……這座塔和延壽有關係,初建者被認為是延壽。」(「永明延壽傳」、《駒澤大學大學院佛教學研究會年報》3,頁79下註[25],1969年)。這座六和塔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更名為開化寺,由延壽的弟子傳法行明負責住持。此外,對於這座六和塔的建設時期,雖有異說,但本文擬略而不談。
| 頁72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好詩道,並撰述了《萬善同歸集》和《宗鏡錄》等書,其字數多達數千萬字[27]。高麗國王(筆者案:指光宗)御覽《宗鏡錄》之後,派遣使節前來致贈金線織成的袈裟、紫水晶數珠、金澡罐[28]。開寶八年的
27. 參照〔表二〕的「著作」欄。
28. 和延壽的生存年代(904~975)相當的高麗國王是光宗(950~975在位)。關於光宗與佛教的關係,根據川越泰博、齋藤弘子製作《高麗史》卷2所載,「〔光宗〕中歲以後,信讒好殺,酷信佛法,奢侈無節」(東京:國書刊行會,1908年,頁33上),同書又記載光宗也建立寺院,例如,大奉恩寺、佛日寺、崇善寺,歸法寺,弘法寺,遊巖寺,三歸寺(同書,頁31上~下,頁32下)。同時,光宗以僧惠居和僧坦文為國師(同書,頁32下,頁33上)。不僅如此,光宗還整頓教團,他「將當時高麗國的佛教教團兩立為禪宗和教宗,使之二元化,而加以整頓。」(章輝玉[1996]「東アジア佛教の相互交流」,木村清孝等編《東アジア社會と佛教文化》頁108,東京:春秋社,1996年)。此外,他也曾派遣使節向延壽贈禮致敬,其時間對判定《宗鏡錄》的成立年代問題影響頗深,必須詳論。請參考筆者的博士論文第二編第二章第二節「著作の相關問題について」。
| 頁73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乙亥年,延壽在住錫的寺院示寂。享年七十二歲,法臘三十七[29]。埋葬地點在大慈山[30],所在建亭,以為標示。
以上是《宋高僧傳》中所載的延壽傳記。在下文中,筆者打算一面參考〔表二〕,一面進行考察。在〔表二〕中,設定了「高麗弟子」以及「入天台」、「授菩薩戒」、「施食和散華」、「懺悔」、「日課百八事」、「拈鬮」[31]、「西方香嚴殿」、「其他」等諸多項
29. 陳垣《釋氏疑年錄》說「錢塘慧日永明寺延壽,餘杭王、宋開寶八年卒,年七十二(904~975)。《佛祖統紀》作開寶七年卒,《釋門正統》作年七十四,《淨土晨鐘》作年九十八,今據《宋高僧傳》卷28及《永明道蹟》。」(1964年版,1988年三刷。北京(北京:中華書局)中華書局,頁190)。又,請參考〔表二〕的「春秋與法臘」欄。本論文遵從《宋高僧傳》及陳氏之說。
30. 大慈山,它位「在浙江省杭州九曜山西南,中峰隆起,旁舒兩翼,圓岡對峙,形似覆釜」(劉鈞仁《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第一卷,頁418)。又,根據《讀史方輿紀要》卷90,大慈山係在南屏山淨慈寺附近(頁3757)。延壽的塔,也就是贊寧《宋高僧傳》文中所謂的「亭」,遠至明代,由大壑元津(《永明道蹟》作者)再度發現,而予重建(參考《淨慈寺志》卷11)。依上述資料而言,原本延壽的塔確實應該是建立在大慈山。
附帶一提,有關為延壽建塔的經濟來源及建塔的時間,清‧際祥主雲《淨慈寺志》卷27中敘述「(開寶)九年正月六日,錢王給幣,為壽禪師建塔於大慈山,樹亭志焉。」但是,此說僅見於此書,然而此書卻是清代的記載。
31. 鬮:也作籤、櫛或「御鬮」,是占卜吉凶禍福的一種方法。它的起源可以遠溯自《周易》六十四卦。若就中國佛教而言,據說為東晉‧帛尸梨蜜多羅翻譯的《灌頂經》卷十「梵天神策經」是提及百籤的最早的資料,頗受注目。在宗鑑撰集《釋門正統》的嘉熙元年(1237)的當時,似乎《天竺靈籤》已廣泛流行(千葉照觀「唐代より現代にいたる觀音信仰」,《觀音經事典》頁307,東京:柏書房,1995年)。從記載延壽的諸多傳記內容來看,十一世紀末所撰述的《新修往生傳》中首度記載「七度拈得淨土鬮」。其後石芝宗曉《法華經顯應錄》及《樂邦文類》,良渚宗鑑《釋門正統》中,也載錄有關「鬮」的記載。筆者認為延壽以「鬮」決定修行方向的事,應該是後世所創作的故事。
| 頁74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目,此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高麗弟子」及「授菩薩戒」、「施食和散華」、「懺悔」等項目。
首先,我們來看「高麗弟子」欄。有關延壽門下有無來自高麗國的弟子一事,在《宋高僧傳》中並未記載,但是從《景德傳燈錄》開始,直到後世的諸多延壽傳記,都認為確有其事。而且,當我們藉由現代研究成果檢證時,在文獻上最早記載延壽門下有高麗國籍弟子的《景德傳燈錄》的記述大致上是值得信賴的[32]。接著我們將檢討「授菩薩戒」的記載。這件事也和「高麗弟子」相同,皆首度見載於《景德傳燈錄》,而在延壽自己的著作《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及歷來相傳是延壽撰作的《智覺禪師自行錄》等書籍中,悉此言及菩薩戒,因此即使延壽為人傳授菩薩戒,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事[33]。但是對
32. 現代學者幾乎都採信《景德傳燈錄》之說。例如木村清孝氏在其《中國佛教思想史》中說「〔延壽〕接受高麗光宗的歸依,他的弟子中來自高麗的也很多,對朝鮮佛教產生極大的影響」(頁201)。鎌田茂雄《朝鮮佛教史》也同樣採用了《景德傳燈錄》的說法(頁185~6)。當我們檢證這一說法的可信度時,韓國方面的資料也非注意不可。此處筆者擬引用韓國學者李鍾益[1977]「韓國佛教における念佛と禪」一文的研究成果。李氏在該文中引用了朝鮮時代毘耶居士許箱《清虛集》的序文以及「原州居頓寺圓空國師碑」,證明了道峰慧炬和圓空智宗(930~1018)均為延壽的弟子(關口真大編《佛教の實踐原理》頁408~9,及李鍾益著[1980]《韓國佛教の研究》頁535~536,東京:國書刊行會。章輝玉[1996]「東アジア佛教の相互交流」頁99~100)。
又韓泰植氏在「延壽門下の高麗修學僧について」一文中,以「寂然國師慈光塔碑」為根據,確認寂然英俊(952~1014)也曾在延壽門下修學過(《印佛研》32-1,頁134~135,1983年)。
總而言之,延壽門下三十六位高麗僧侶的名號雖然依然無法一一確認,但是至少已經能確認上述三位國師確實存在。因此,韓氏在論文中作出下述的結論,他說「我們可以說,當時延壽的佛法帶給高麗佛教界的影響非常大。」由此可知,延壽門下有高麗弟子之說,並非《景德傳燈錄》的臆說,它是經得起實證的事實。
33. 參照:《宗鏡錄》(《大正藏》48,頁886下,頁921中),《萬善同歸集》(《大正藏》48,頁969下),《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111,頁160下,頁165上)。又,此處筆者想說明的是,「菩薩戒」是天台宗所實踐的重要宗教活動(湯用彤氏甚至明言「於戒律,天台宗為菩薩戒之提倡者。」(同氏《隋唐及五代佛教史》頁264)。當然延壽所隸屬的法眼宗也傳授菩薩戒。例如,擔任淨慈寺第一世住持的永明道潛(?~961)即曾經為忠懿王錢弘俶傳授菩薩戒,所以延壽的情況究竟是否為接受來自特定宗派的影響的結果,目前雖然還無法下結論,但是延壽一度在天台山修行,所以受到天台宗的影響也並非不可能。再加上,利根川浩行氏曾在「中國宋代以後の菩薩戒」一文中說,「菩薩戒並不單止停留在戒律問題的層面上,在中國佛教裡,它也承擔了作為來世往生(先不論到底是彌勒淨土或是阿彌陀淨土)的機緣的功能」(《大正大學研究紀要》71,頁179,1986年)。綜合考量,延壽的戒律觀以及「授菩薩戒」的狀況,有必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 頁75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於授菩薩戒的時期和地點──在《景德傳燈錄》文中認為是,開寶七年(974,也就是延壽圓寂的前一年)在天台山傳授,但是這一說法還沒有其他的典據能支持,也就是尚未能獲得確認。又,「施食和散華」欄所載的施食和散華這二件事見載於《萬善同歸集》和《智覺禪師自行錄》[34]。最後想討論的是「懺悔」。延壽實行懺悔法門一事的確屬實,但是對於他所實行的法門卻各典籍呈現各說各話的情形,例如《宋高僧傳》記載為「方等懺」,而屬於淨土宗系統的王古《新修往生傳》和禪宗系統的曇秀《人天寶鑑》,天台宗系統的宗曉《樂邦文類》、志磐《佛祖統紀》等典籍中則記載為「法華懺」。當然延壽也有同時實行這兩種法門的可能性(請參考注[20]),但是筆者認為延壽經常付諸實踐的懺悔法門終究應該是法華懺[35]。
34. 關於「行道」,參見《萬善同歸集》卷上(《大正藏》48,頁964中,963),《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111,頁157,頁159)。關於「散華」,參見《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111,頁160)。關於「施食」,參見《智覺禪師自行錄》百八佛事之第八十五條(《卍續藏》111,頁163下)。又,關於「彌陀化身」的記載見於大壑《永明道蹟》(《卍續藏》146,頁982上),同書的951年項目中(《卍續藏》146,頁980下)記載忠懿王錢弘俶建立永明寺,由時間上而言,這一則「彌陀化身」的記載無法成立。
35. 關於法華懺,在《萬善同歸集》卷上(《大正藏》48,頁963下、頁964上、964下、965下),《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111,頁154下)兩部書中,延壽均曾言及。此處,筆者將主要著眼於構成法華懺內容的懺六根和五悔。這兩項內容在《萬善同歸集》等延壽自己的著作中也有所涉及。
關於懺六根,參考《萬善同歸集》卷上(《大正藏》48,頁966上),《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111,頁155下,頁161下~163上)。關於五悔,參考《萬善同歸集》卷上(《大正藏》48,頁961中,頁965下),《宗鏡錄》卷88(《大正藏》48,頁896上),《智覺禪師自行錄》(《卍續藏》111,頁161下~163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書的見解幾乎都是引用天台宗的解釋而作的說明。懺六根的原始典據雖然是《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但是延壽卻引用智顗《法華三昧懺儀》第七以說明其作法(對比:《大正藏》46,頁952中~953中,及《卍續藏》111,頁161下~163上)。五悔的情況也相同。從上述情況來看,我們應該可以說,延壽所實踐的法華懺法係受到天台宗的影響(詳細內容請參考拙稿「永明延壽の懺悔觀」、《印佛研》45~2)。
又,關於延壽修行法華懺法之事,應和見載於宗曉《法華經顯應錄》、《樂邦文類》,良渚宗鑑《釋門正統》等典籍中的內容有關聯,即和延壽行道時,「普賢〔菩薩〕前供養蓮華忽在手」的記述有所關係。其因何在。此因,有許多人在實踐法華懺法或法華三昧時,能感應普賢菩薩現身於夢中。相關類例見載於《續高僧傳》及《神僧傳》、《大明高僧傳》(《大正藏》50,頁865上。同書,頁585中25,頁688下28。又同書,頁983下7,983下13)。其實關於這一點,筆者認為猶有進一步深入探討論究的必要。
| 頁76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的看法。這就是,與其他典籍相比較的結果,《宋高僧傳》既在成書年代上(988)是最接近延壽的生存年代(904~975)的一本,而且它所記載的內容也可信度極高。但是話又說回來,其他典籍所記載的內容就一方面而言,有根據有依憑的也確實比比皆是,然而也有從歷史事實的角度檢視的話,頗令人難以置信的記述(例如,冥府禮敬延壽),像這類的記載則有必要一一考證。此外,當我們全面檢視延壽的各傳記內容時,由其中也可看出宗派性的傾向。舉例而言,關於「拈鬮」的記事,自從首度見載於屬淨土系統的王古《新修往生傳》以來,那些屬於天台宗系統而重視淨土法門的宗曉《法華經顯應錄》、《樂邦文類》,良渚宗鑑《釋門正統》以及志磐《佛祖統紀》等典籍中都同樣見載。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有關「法華懺」或「法華三昧」的記載上,也就是說,這件事也同樣見載於屬於天台宗系統而重視淨土法門的各典籍。而「上堂法語」的記載情況則是僅只殘留在屬禪宗系統的各典籍裡。至於「西方香嚴殿」及「日課百八事」的二項內容卻是全然僅出現在以王古《新修往生傳》為首的屬淨土系統及天台宗的各典籍裡。當我們比較並檢討完記載延壽個人的諸多傳記之後,所呈現出來的事實之一是,雖然一般的理解認為宋代以後的中國佛教乃以融和統一諸宗為基本性格,其實仔細探討時,宗派性立場實際上仍在某種程度上殘留著。另一件事實則是,隨著時代下降,淨土法門在天台宗內部的影響力日漸增強。至於延壽,可說是試圖融合禪與天台的一位[36]。
36. 參考:荻須純道〔1958〕「趙宋佛教復興の一考察」、《印佛研》6~1。
| 頁77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表一〕永明延壽各傳記的關係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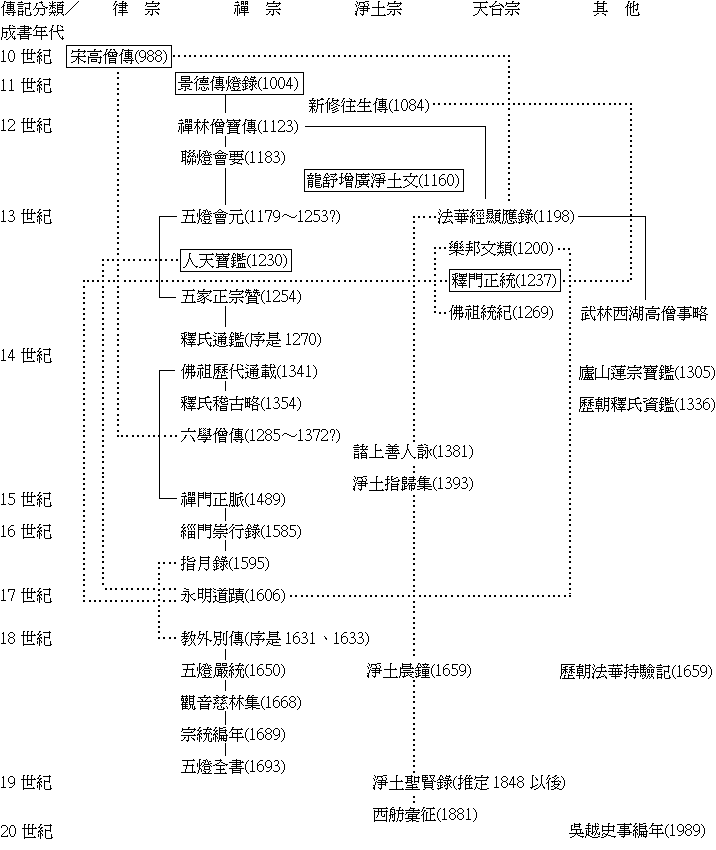
| 頁78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表二〕永明延壽各重要傳記的比較表
【凡例】
本比較表主要係依據在檢證永明延壽傳記上,最重要的五部文獻所記載者排列而成。另外,其餘的相關文獻,若所記述的內容、項目是其他文獻所未見載的新說,或者是值得參考的內容,原則上載錄於「備考」欄。
1. 由於異說屢屢可見,因此各項目的順序並非依據年代先後嚴格地排列,而是專依《宋高僧傳》的敘述先後為序。
2. 同一項目裡,若有數項內容值得載錄時,係依著作年代之先後予以排比。
3. 關於所依典據,係使用如下之略稱。
| 僧寶傳 | 慧洪《禪林僧寶傳》(《卍續藏》137,頁478下~481上) |
| 顯應錄 | 宗曉《法華經顯應錄》(《卍續藏》134,頁865上~下) |
| 會元 | 大川普濟《五燈會元》(《卍續藏》138,頁366下~367下) |
| 統紀 | 志磐《佛祖統紀》(《卍續藏》49,頁264中28~265上7) |
| 武林 | 元敬‧元復《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卍續藏》134,頁473上~下) |
| 資鑑 | 熙仲集《釋氏資鑑》(《卍續藏》132,頁169下~170上) |
| 稽古略 | 念常《釋氏稽古略》(《卍續藏》49,頁857上9~中12) |
| 道蹟 | 大壑元津《永明道蹟》(《卍續藏》146,頁976下~987上) |
| 編年 | 諸葛計等《吳越史事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 |
4. 本〔表二〕中載錄了為數不少的未見錄於〔表一〕中的文獻。例如:
屬淨土類典籍的袾宏《淨土資糧全集》、袾宏《雲棲法彙》(往生集)、弘贊《六道集》等,另外,屬地方志類典籍的有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張思濟《餘杭縣志》、傅玉露等編《浙江通志》等,而屬佛寺史志類的則有釋際祥《淨慈寺志》、《雪竇寺志》、《天台山方外志》、《天台山志》卷八、《武林理安寺志》卷1、徐增《靈隱寺志》卷2及卷3等等。但是,由於這些資料、文獻,有的是時代相當晚的作品,有的是性質比較特殊的資料,所以筆者僅依需要而載述之。
| 頁79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
書名/項目 |
宋高僧傳 |
景德傳燈錄 |
龍舒淨土文 |
人天寶鑑 |
釋門正統 |
備 考 |
|
名字與出身 |
王‧錢塘 |
王‧餘杭 |
名延壽‧本丹陽人、後遷餘杭 |
先丹陽人,父移居錢塘 |
字沖元,號抱一子 |
諱延壽(僧寶傳) |
|
履歷 |
為吏、軍須 |
年28,華亭鎮將 |
初為縣衙校 |
儒生 |
|
北郭稅務專知官(顯應錄)餘杭庫吏(道蹟) |
|
出家師長 |
翠巖令參 |
翠巖遷龍冊寺 |
|
年34,往龍冊寺出家 |
同寶鑑 |
30歲出家(道蹟) |
|
放生 |
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 |
朝放諸生類 |
多折官錢放生 |
|
乞西湖為放生池 |
曾放生魚萬尾(僧寶傳)盜官錢放生(東坡志林、顯應錄) |
|
誦法華經 |
計一萬三千許部 |
計一萬三千許部 |
少時誦法華 |
|
|
|
|
住雪竇 |
誨人坐諷禪誦 |
住持雪竇 |
初住資聖 |
入雪竇十年 |
孤猿叫落中巖月(會元)(注3) |
|
|
造塔像 |
勸人造塔像自無貯蓄 |
|
|
|
於淨慈石崖鐫刻聖像 |
|
|
歷住 |
|
960 任靈隱一世 |
住持永明 |
同景德 |
同景德 |
|
|
著作 |
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鏡等錄數千萬言 |
宗鏡錄百卷,詩偈賦詠千萬言,播於海外 |
萬善同歸集,宗鏡錄等共數萬卷 |
宗鏡錄百卷大乘悲智願文 |
對雪吟,講德詩,齊天賦,五賦(注4) |
宗鏡錄被勅入大藏(顯應錄) |
| 頁80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 垂誠文 | 流行(稽古略) 有四偈、勸禪人兼修淨土(諸上善人詠) 著作共97卷(道蹟) 著抱一子若干卷(編年) |
|||||
| 海外歸敬 | 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贈袈裟等 | 高麗國王遣使申弟子之禮,贈袈裟等 | 同宋傳 | 開寶元年,高麗國上書歸敬並遣僧問道,敘弟子之禮(資鑑) 事在開寶六年(淨慈寺志) |
||
| 葬地與塔 | 葬於大慈山,樹亭 | 塔於大慈山,宋太宗賜額:壽寧禪院 | 塔於大慈山 | |||
| 春秋與法臘 | 春秋72、法臘37 | 春秋72、法臘42 | 春秋74、法臘40 | |||
| 住永明 | 永明妙旨(注5) 偈:欲識永明旨(注7) 永明家風(注8) 問:如何是此經?(注9) 問:大圓鏡?(注10) 居永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 |
謝世歸華頂峰(注6) | 同坑無異士(聯燈會要) 居永明十五年(統紀) 顯德元年忠懿王建永明寺(道蹟) |
| 頁81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 高麗弟子 | 36人,歸國後各化一方 | |||||
| 入天台 | 開寶7年入天台度戒萬餘人 | 居永明十五年,移天台(武林) 入天台(會元) |
||||
| 授菩薩戒 | 常為七眾授菩薩戒 | 普為四眾授菩薩戒 | ||||
| 施食與散華 | 葉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華行道 | 一生散華供養 | 時稱慈氏下生(新修往生傳) 彌陀化身(道蹟) |
|||
| 懺悔 | 行方等懺 | 於國清修懺 | 入國清修法華懺 | 行法華懺(新修往生傳)於國清行法華三昧(顯應錄) | ||
| 日課百八事 | 日課百八事 | 入雪竇十日,日課百八事 | ||||
| 拈鬮 | 一鬮云,誦經萬善生淨土 | |||||
| 西方香嚴殿 | 忠懿王為立西方香嚴殿(顯應錄) | |||||
| 其他 | 寶覺編《冥樞會要》 | 忠懿王請出山,賜號智覺 | 示寂後,賜號智覺(統紀)崇寧中追諡宗照禪師(統紀,咸淳臨安志) | |||
| 講律,行布薩 | 今淨慈寺方丈曰宗鏡堂(稽古略) | |||||
| 一生隨處建法華堂(道蹟) |
| 頁82 | 永明延壽傳記研究 |
法光學壇第五期(2001) |
| 於慧日峰誦法華經,感諸天雨華,為雨華台(道蹟) | ||||||
| 為靈隱中興之祖(道蹟) | ||||||
| 建隆元年,忠懿王贈號智覺(淨慈寺志) |
【注】
(1) 師上堂曰:雪竇遮裡、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景德傳燈錄』卷26、『大正藏』51、421下19~21)。
(2) 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景德傳燈錄』卷26、『大正藏』51、421下21~23)。
(3) 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雪深處坐禪僧。」(『五燈會元』卷1、『卍續藏』138、366上11~13)。
(4) 著五賦:五賦即神棲安養‧法華靈瑞‧華嚴感通‧觀音應現‧金剛證驗。(『釋門正統』卷8、『卍續藏』130、898下18~890上1 )。
(5)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勿交涉。(『景德傳燈錄』卷26、『大正藏』51、421下25~27)。
(6) 渴飲半掬水、飢餐一口松。胸中無一事、高臥白雲峰。(『人天寶鑑』、『卍續藏』148、141下2~4)。
(7) 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景德傳燈錄』卷26、『大正藏』51、421下27~29)。
(8) 問:學人久在永明、為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景德傳燈錄』卷26、『大正藏』51、422上1~3)。
(9) 問:承教有言、一切諸佛及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景德傳燈錄』卷26、『大正藏』51、422上5~8)。
(10) 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景德傳登錄』卷26、『大正藏』51、422上8~9)。